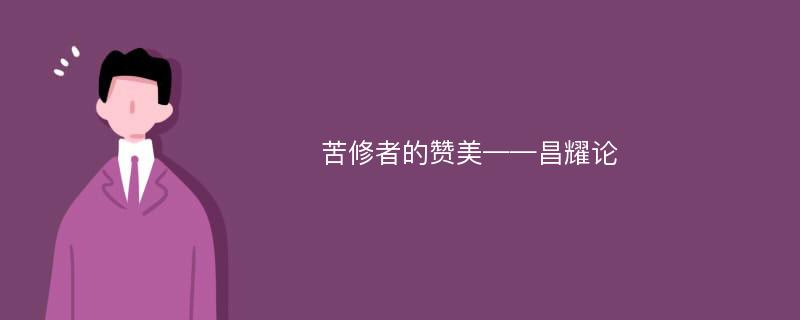
论文摘要
昌耀创造了一个神话,他也要通过神话来表达他的所思所想,追求一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因为他知道,对于人的灵魂具有震撼力的是神话而不是故事(即单纯的个人受难史),他要将之上升到一个与神话对应的结构。如《大山的囚徒》,如《慈航》等,是一种象征、一个寓言:通过陈述真事来虚构神话,创造一个人抵抗恶的神话。他将神话根植于厚重的现实之中,通过现实世界的无数准确逼真的细节,让日常生活的凄风苦雨吹拂其间,从而展现出与恶相搏之惊心动魄。这是寻常“百姓”的英勇和尊严,虽无叱咤风云之态,却有顶天立地之气。他的意义正在这里:单个的昌耀是软弱无能的,但是这个“百姓”的昌耀、“神话”的昌耀却是力量巨大的。他以“百姓”得以存留,以“神话”显其威力,而这威力正来自于其苦心经营的“百姓”这个神话,也说出了现实人生的悲壮和生命的不息。同时,他造了一个“唐·吉诃德军团”,这就是他的“百姓”、他的“人民”。而他的“行脚僧”的神话,对应的是宗教的苦修和佛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倒是这个“诗人”的头衔,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他多少是并不在意的(“……一味受人访谈未必增加作家存在的价值,但一味受人冷遇也未必是作家之初衷。”),只是他在俗世行走和发言的一个身份。但他需要这个“诗人”的身份,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把“百姓”与“行脚僧”统一,也只有“诗人”这个身份,才能包容二者于其中。“诗人”是一座桥,它架通了“百姓”和“行脚僧”,让肉体的苦难获得了精神的意义。昌耀及其诗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由其人、其诗、其事构成了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其人其诗其事。而正因为其诗其人其事是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现象,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有时截然相反,但从精神现象的意义上,它们又是统一的,这正是其人其诗丰富性的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自身的矛盾、软弱,也照见了世人的复杂、暧昧。也只有从精神这一层面,我们才能不只是单纯地吹捧或棒杀一个诗人,而是看到一个人的局限和自由,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局限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