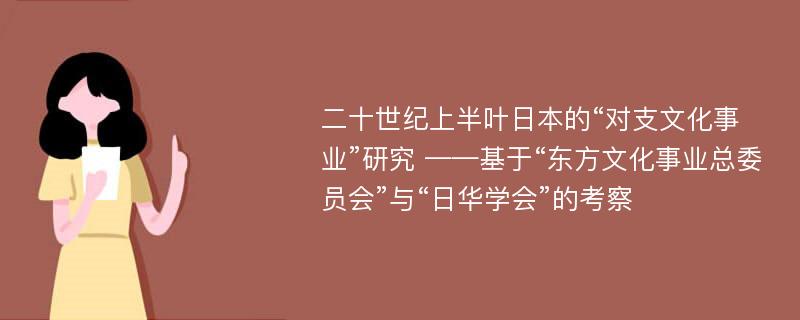
论文摘要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日国家关系由摩擦频发走向战争的历史阶段,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西原借款”不断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向中国要求特殊权益,侵华态势日益明显,使国人深受伤害,反日、排日情绪高涨,各地纷纷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试图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此时日本“大正民主”的余温尚存,部分日本实业家和文化人提议利用庚款实施“对支文化事业”,通过该事业改善两国关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日本的态度出现了游离。日本外务省在1923年3月颁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确定庚款的主要用途限定于日本对华的文化、学术工作以及留日学生、在华日本医疗文化机构的资助等。《特别会计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强烈反对,中日之间矛盾集中在庚款的使用权上。日本根本没有将庚款交由中方使用的想法,凭借《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其绝对控制在自己政府手中。对此,中国教育、文化界谴责“事业”,认为该“事业”实质就是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坚决要求日本做到真正的退还庚款,要求把握“事业”(以下简称“事业”)的主导权。日本外务省极力否认“事业”的文化侵略性,并打出“超越政治”、“发展东方文化”的旗号,同时强压中国外交部共同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推进“事业”在华的标志性项目——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建设。但“总委员会”中方委员在日本军部挑起的济南事件的背景下宣布退出,“事业”从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重新回到日本单方运作的“对支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日方委员撇下刚刚开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核心项目——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返回日本继续延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名誉,用庚款建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京都研究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为其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研究经验。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对支文化事业”,消弭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对立情绪而设立的“文化”工作基地,同时日本外务省积极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加紧创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意图还在于通过该渠道的名目将庚款操纵在自己手中。“日华学会”原本是依托“支那留学生同情会”的转让基金起步的民间团体,后来逐步染上半官方色彩,成为日本外务省控制的外围团体。自1918年成立以来到1945年解散的近三十年里,负责担当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为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宿舍、管理留学预备教育机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的文娱活动以及接待中国访日教育、文化团体等,与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团体保持着紧密联系。1923年“日华学会”作为对华留学生工作团体开始接受“事业”的重点经费资助,在中日教育、文化往来活动中提供服务,起到了一定的交流作用。但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日华学会”受中日关系的影响,在“事业”主体框架下沦为服务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文化工具。本论文以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为时代背景,从中日双方的史料入手,运用实证的调查方法考察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和“日华学会”的活动轨迹,并结合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应对态度,浮显出日本“对支文化事业”的整体结构,在综合中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加以客观、具体的分析,从而为进一步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日教育文化关系的基本面貌和结构特点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侧面。“对支文化事业”的实质并非是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亚洲文明,而是为日本对华政策服务的,欲达到染指甚至控制中国文化研究和教育事业的目的,这是当年中国教育、文化界极为警惕和反对的。不论从日本外务省在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中日合作过程中所表现的态度,还是从创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意图来看,“对支文化事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这种矛盾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外务省的缓和方针与军部的强硬态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②部分文化、实业界人士的对华亲和态度与日本侵华总方针构成的局部与整体的矛盾;③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敬与对现实中国蔑视的日本文化人自身的中国认识矛盾。这三重矛盾关系是引发中日教育、文化摩擦的重要理由,也是导致“对支文化事业”最终演变为日本侵华的文化工具的主要原因。文化、教育交流是国家间维系长期友好关系的基础,是构建不同国家间的人与人之间沟通合作的有效方式。“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和“日华学会”客观上为维系两国教育、文化界的交流做出了具体工作,但结果却是“对支文化事业”转变为“对支文化侵略”。这证明了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需要对等的政治关系和作为交流主体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互信机制。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利益至上的、日本本位主义的交流并不是真正的中日交流。中日两国只有站在互相尊敬、互为平等的立场上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