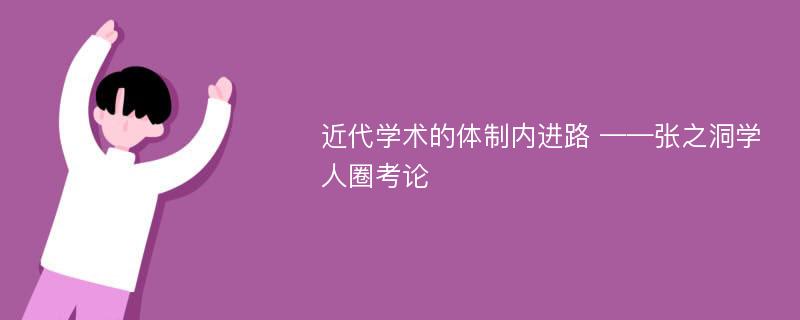
论文摘要
本论文的考论对象,是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吸收外来新知识、新经验较有效率,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其中的张之洞学人圈,虽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开创了近代学术转型在本土语境下的“缓冲模式”。同光之交活跃于京师的“清流”,是张之洞学人圈渊源所在。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为“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辟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此期间幕府的诗酒交游日渐繁盛,同光诗学的“三元说”于焉生成,却仍以追怀“清流”风气、再现“文盛之世”为主题。在传播京师新学风的同时,张之洞学人圈亦注意与晚近地方学统相整合。张之洞早年督学,深受乾嘉以来经古书院、官书局传统影响,致力于汉学地方化;但在履任粤督后,却开始尝试超越阮元等汉学名臣。经过对陈澧汉宋调和之学的再阐释,新设广雅书院更带有折衷取向。同一时期,与“东塾学派”同样主张折衷汉宋,但思路有所出入的南菁书院学风,亦为张之洞学人圈所汲取,却剔除了其中过于专门化的部分。“东塾”与“南菁”成为张之洞督鄂以后倡导文教的两大资源,加之两湖地域固有的经世学风,以及此期业已活跃于江南沿海的新学风气,形成两湖书院中各地方学统累积、竞争甚至纷争的局面。张之洞学人圈对于近代学术的持久影响,更在于学制设计。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生成,伴随着新教育的统系之争,而其背景则为南北督抚的派系分化。其中,尤以江、鄂联合与北洋对峙的局面最为显著。庚子事变后,清廷重启新政,“江鄂”与“北洋”的教育新经验先后进入清廷文教中枢的视野。二者在搬用日本学制的大前提上并无异议,但关于如何在新学制下保存旧学统,却依其固有的学统区分,呈现出“尊经”与“重文”的分歧。此期间海外革新势力活动频繁,京、外各地学潮亦开始涌动。于此背景下,张之洞奉旨参与学制改章,在引进明治日本学术经验的同时,亲自主导了经学及“中国文学”课程的制定。张之洞学人圈之所以能在文教变革中得风气之先,主动吸收日本经验实为关键。清末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主张日文翻译的兴盛,文章写作上出现了有关“日本文体”及新名词的讨论。受日本军部及兴亚团体鼓动,戊戌前后张之洞方面曾是提倡“东学”、“东文”的先驱;但在戊戌政变后,为了与康梁势力切割,同时更受近代国族意识的影响,张之洞系统在维持对日联络的同时,却对来自日本的学术、出版、政治新经验不无保留。曾经一度感动中日双方朝野人士的“同文”意识,遂日渐淹没于体现国族特性的“国语”、“国文”言说,并最终凝固为清末学制规划中同时带有近代国族意识与传统政教理念的“国文”学科。本论文将从学风、学制、文体三方面考论张之洞学人圈引进近代新知识、新经验的“缓冲模式”,以试探近代学术、文教在体制内转型的别样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