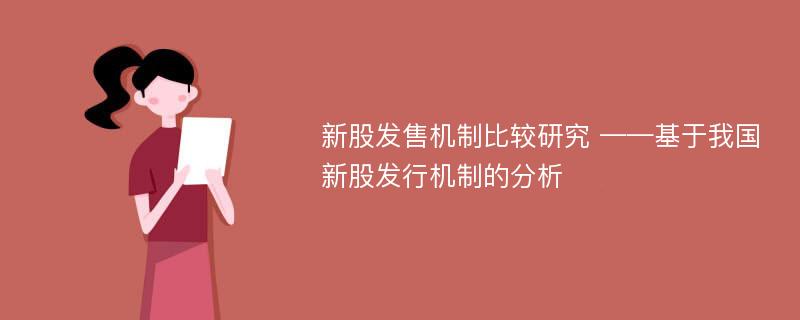
论文摘要
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指在一个流动性充分的市场上首次出售证券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融资行为。公司通过上市,可以在流动性良好的股票市场上以低于私募的成本来筹措更大规模的股本金,同时也为现有股东的股本变现提供了通道。除此之外,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大大提高。从1980到2001年,美国新股发行数量超过平均每个交易日1只,总共募集了4880亿美元(按2001年价格计算),每只新股平均融资7800万美元(Ritter and Welch,2002)。在我国,股票市场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发展相当迅速,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目剧增,截至2006年10月,境内上市公司数(A,B股)1406家,市价总值62025.71亿元。首次股票公开发行是金融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块重要领域。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股发行的短期抑价现象引起了金融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Logue(1973)和Ibbotson(1975)等学者最早发现和记录了这种异常高的首日收益率。此外,许多学者利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亚洲的新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如欧美成熟的股票市场,投资都会获得初始超常的回报率,只不过后者较前者程度较低而已。我国学者利用A股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新股发行初始收益率远高于成熟金融市场的发行初始收益率。相当高的首日收益率说明我国股票市场低效运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西方学者上世纪80年代末建立经济模型将新股发售机制同新股发行抑价程度联系起来,说明了两者的相关关系。新股发售机制是指确定新股发售价格并向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方式或过程。自此关于新股发售机制的选择和设计的研究成为金融经济学中的重要命题。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利用各国金融市场数据证明发售机制与新股发行初始收益率相关。此外,90年代以来,新股发售机制使用的全球趋势是:新股发售机制方面最重要的趋势就是簿记制“驱赶”固定价格制和拍卖制,成为全球居于主要地位的新股发售机制。这一趋势的确立更进一步促进了对发售机制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建立经济模型对不同发售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发售机制的本质特点,回答监管层/发行人如何选择发售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一定经济假设下推导出新股发售机制的最优设计。再者,由于簿记制的使用日趋广泛,簿记制下承销商如何“歧视性配股”成为新股发售机制领域关注的热点。最后,不同国家金融市场市场上簿记制操作的各自特点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比较研究法,对簿记制和两种拍卖机制:统一价格拍卖制和歧视价格拍卖制建立信息经济学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没有对另一种发售机制,固定价格制建模,因为从本文第三章的文献评述部分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固定价格制的特征已经达成共识。既固定价格机制的优势体现在:首先,避免了累计投标询价中高昂的路演成本,信息成本低则进行信息搜集的投资者更多。固定价格制在实践中仍在较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小规模发行以及投资者搜集信息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其次,预先缴款的特点保证了申购资金及时到位,同时可以为发行人带来利息收入。Benveniste and Busaba(1997)认为固定价格机制具有融资收入比较确定的好处,发行人的风险厌恶特征会使得发行人倾向于选择固定价格发售机制。因为没有哪种机制绝对占优——发行人的偏好应该主要取决于新股发行的风险和发行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1)公司面临的价格不确定性越大,越可能偏好于采用固定价格机制;(2)公司如果更加关注新股发售的风险,也可能偏好于采用固定价格机制。Jagannathan and Sherman(2004)全球发售机制选择的实证数据表明固定价格机制的使用在各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相对于固定价格制,关于簿记制和拍卖制的争议更大。不少关于拍卖制建模的文献认为拍卖制下能够实现新股发售定价和配股过程的最优;来自经验研究的证据也表明拍卖制下发售抑价程度并不显著高于簿记制下的发售抑价程度,为什么实践中各国纷纷放弃了拍卖制而使用簿记制呢?实践选择的结果表明簿记制必然有相对拍卖制而言的特定优势特征。本文中本着这样的思路,对簿记制和拍卖制在同一经济环境下建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一个数值例子帮助理解簿记制和两种拍卖机制的主要区别。模型主要结论是簿记制相对拍卖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簿记制下承销商对整个发售过程的控制能力更强,表现在承销商能有效的控制参与发售过程的投资者数量、“信息获取”和配股;换言之,簿记制下承销商能够有效控制发行风险。明确地说:1)承销商能够有效控制信息成本;2)避免有效申购不足而导致发行失败。簿记制下发售过程所面临的风险小于拍卖制在于承销商能够保证一定数量的投资者认真对待发售、严肃评估新股并最终参与发售。如果新股“热发行”,承销商能够保证严肃的常规投资者得到分配以补偿他们的信息成本。而拍卖制下承销商却无法保证这一点。模型也显示,潜在投标人数的增加并不能消除拍卖制下新股发售的风险,既不能有效降低抑价程度也不能减少发行失败的可能性。更多潜在投标者可能降低单个投标者的预期利润因而使得投标者放弃评估新股和竞标的可能性增大。本模型没有使用“最优机制设计”的范式,因为本文并不否定拍卖制下发售过程能够达到最优,而是认为拍卖制下发售过程很少能够达到最优。再者,比较研究的范式能够更好的理解不同发售机制的本质特点。本模型的结论同时也能够为Jagannathan and Sherman(2004)的经验证据提供解释。此外,本文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实际操作中的簿记制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拍卖机制的改进设计。由于模型中假设承销商和发行人利益一致并且知情投资者购买信息的行为是相互独立的,换言之,模型并不允许知情投资者合谋的情况。但是在实际的发售过程中,上述假设可能不成立。因此,实际操作中的簿记制可能面临:(1)“歧视性股票分配权利”可能导致了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谋。实际操作中这种股份差别分配机制实质上是发行中各主体利益分配的集中体现:承销商使用他们的分配权去从投资者那里获取信息,这可以减少平均抑价,增加发行人的收益;知情投资者通过重复投标,在有利发行或热发行中得到多数股份的分配,而在冷发行中则刚好相反。这种有差别的股份分配所涉及的利益问题也可能使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合谋,损害发行人的利益。(2)机构合谋报告“错误信息”或“隐藏真实估价信息”的行为会导致新股发售误定价。发售过程中出现机构合谋的可能性往往与一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结构和发售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有关。就拍卖制的改进而言,模型的结论是拍卖制下发行人/承销商面临的最大风险为无法估计实际参与发售的投标者人数进而无法很好控制抑价程度以及保证发售成功。本文通过指出Google2004拍卖通过弥补上述不足的案例说明拍卖机制的优化方向。最后,本文对我国新股发行市场状况和新股发售机制的历史变迁和现状进行了评述。本文回顾我国股票市场自93年以来发售机制的变迁,经历了行政化—市场化—非市场化—准市场化的过程。从行政化发售机制到法人配售询价机制、拍卖机制、二级市场配售以及新股询价制等市场化发售机制的尝试,表明了我国新股发售机制市场化改革过程的曲折,同时也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最终选择的模式是新股询价机制。本文指出新股询价制是传统簿记制在我国市场上的变形。在我国股票市场逐渐走向成熟后,新股询价制必然会逐渐向传统簿记制靠拢。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当前的新股发售工作,监管层可考虑允许规模较小的发行选择使用固定发售机制;逐渐加大对机构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并允许承销商有一定配股权并促进新股询价制相关的配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本文对新股发售机制领域的研究做了系统整理、分析和评述,并总结出其代表性文献的研究思路、研究重点、主要方法及结论;之前我国学者并没有对此领的文献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做过系统分析和评述。(2)本文基于比较研究的范式,对簿记制和两种拍卖机制建立经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一个数值例子进一步理解不同拍卖机制之间的本质差异;我国学者中利用信息经济学模型分析发售机制的文献较少。(3)对我国使用过的发售机制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指出发售机制的选择和设计受制于一国金融市场特征。新股询价制是簿记制在我国市场上的变形,随着我国股票市场逐渐走向成熟,新股询价制会向传统簿记制靠拢。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本文致力于对新股发售机制的各自特点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论述;但就新股发行来说,发售机制与新股发售定价具有较高的关联度,本文由于水平和篇幅有限,并未对新股发售定价方法展开论述。(2)由于资料和相关文献不足,同时笔者水平有限,本文对国内新股发售机制运用的研究仍不够深入;(3)本文选题角度较新,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此领域文献的收集可能不够全面,因此本文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论述存在一定缺陷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