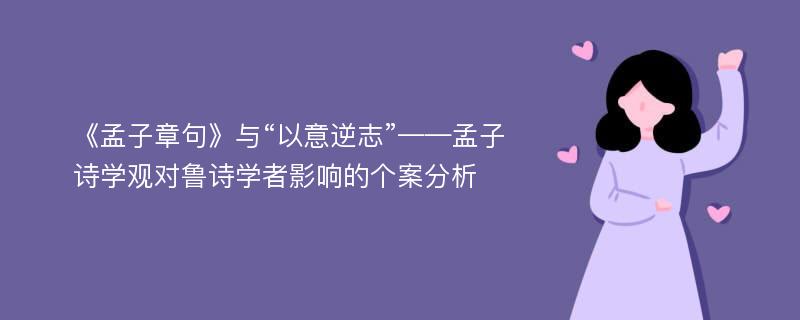
李华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人们在论及孟子诗学在汉代的影响时,往往仅从诗学发展角度来探讨其影响。然而通过对赵岐的《孟子章句》中的章指设置和篇章结构的分析可见,《孟子章句》的整体设置与孟子的“以意逆志”思想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不仅反映了孟子诗学观点在汉代影响之广泛而深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赵岐《孟子章句》中篇章设置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孟子章句》;以意逆志;诗学
周广业《孟子四考》曾称赞说:“媺哉,汉之尊经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贤传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诸子也,而通义得述孟子。”[4](P101)这一观点指出,为《孟子》做注是汉儒对孟子的最大推崇方式之一。而赵岐不仅作《孟子章句》,将孟子推尊至“亚圣”地位;并且盛赞孟子在《诗》学方面的创获,即“尤长于《诗》《书》”;最为重要的是,其《孟子章句》章句设置、训释体例也得益于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承传。
一、赵岐对“以意逆志”的理解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的一则记载,孟子弟子咸丘蒙以《大雅·云汉》询问孟子,如果按照《诗》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判定,那么舜为天子,其父应不应该以臣道侍奉舜。面对这一疑问,孟子提出了“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以意逆志”说,即对《诗》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对字面的理解,而应当深入推求字面背后的深层含义。对此,赵岐解释为: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辞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志在忧旱灾,民无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非无民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4](P638)
赵岐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的阐释中,有一处尤应引起重视,赵岐理解“以意逆志”说为“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张伯伟先生指出,赵岐对“以意逆志”的理解基于人性论的角度,其中所“逆”,即是从自身角度开始的“推求”[2]P180,《孟子题辞》中对“以意逆志”说的理解再次证明了这一倾向:“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而赵岐强调阅读者在文本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正是抓住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精髓。换句话说,阅读者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甚至要远远大于作者本人在文本阐释中所起到的作用。孟子提出这一观点,在于确立诗学阐释者在《诗》义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赵岐领会了孟子的这一阐释意图,并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中所传达出的对阅读者的主体作用的强调扩展到了更为深广的文本阐释领域。
在彰明创作主旨的《孟子题辞》中,赵岐就明确表明自己对“以意逆志”的赞同与承袭: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赵岐指出“以意逆志”在于使后人深入探求其文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一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诗》,而是适用于对长于譬喻的孟子的解读。这是赵岐使用“以意逆志”以注《孟子》的明确宣言。在具体的注释过程中,赵岐也坚持了这一做法。
二、《孟子章句》的章指运用对“以意逆志”的贯彻
在《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上,赵岐运用了“以意逆志”的智慧。通过章指,概括出了每一章的微言大义。赵岐自述《孟子章句》的篇章设置特点在于“具载本文,章别其指”。所谓“具载本文”,即把经传连文,直接把传置于经后;而“章别其指”,则是在每章末尾撰写章指,总括该章整体意义。虽然类似的做法,在赵岐之前的经籍注释中也有出现,例如《毛诗序》、《楚辞章句》的篇序等,但是明确冠以“章指”之名,并在每张最后分析该章旨意的做法,却始于赵岐。阮元在《孟子注疏校勘记序》中便对赵岐设置章指的功劳给予高度推崇,指出章指中蕴含了推求微言大义的功能:“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3]附校勘记清人周广业在评价《孟子章句》时也曾指出:“章指者,櫽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数万,其指数千,知文必有指。赵氏因举以为例。”[4]P102这两处论断不仅是对赵岐以章指注《孟》的最好概括,而且也透露出赵岐设置章指的深层意图:“章指”一词,最初源于董仲舒对《春秋》的理解,而汉儒重视《春秋》,正是因为汉儒相信孔子于春秋》之中,蕴含着微言大义:“文多数万,其指数千”,这恰恰也是汉人专注于对经典的解读和阐释的原因之一。而阮元与周广业此处把赵岐做《孟子章句》与董仲舒阐释《春秋》相对比,显然已经窥破赵岐注《孟》的奥秘:即赵岐试图在《孟子章句》中阐发出《孟子》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或者以此为载体传达出自己的个人思想观点。而这一意图,也恰恰与赵岐对孟子“亚圣”的定位若合符节。
三、《孟子章句》的篇章设置对“以意逆志”的集中彰显
赵岐把孟子的思想主张归纳为:仁义、礼、孝、性情、心等几个方面,并认为《孟子》的篇章设置正是由此而定。《孟子》介于语录体和传论之间,其中既有旨意明确者,也有连缀搜集者,赵岐对《孟子》七章的章指强作分类,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南宋林之奇《孟子讲义自序》就指出“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文字多寡,篇名先后,出于一时之偶然,不可泥也。”[1]P102不仅如此,赵岐还从数理的角度指出,《孟子》分为七篇,正是与天上的“七纪”;而孟子的篇章设置,又恰恰与三时的日数相当。而字数的多寡,又恰恰与五常之道相应。从数理的角度阐发《孟子》的创作意图,充斥着的正是汉代学术界所流行的气运终始的五行观,这明显是站在了汉儒的立场对孟子创作主旨的附会和“以意逆志”。
赵注中“以意逆志”的特点虽然前贤并未道破,但是由此引发的流弊却广为学者诟病,例如朱熹便认为赵注“拙而不明”[5],近人胡毓寰指责赵注“于义理方面确多肤泛之弊”[6]P85,今人黄俊杰先生在肯定赵岐注《孟》之功的同时,也认为赵岐由于过于关注对政治意图的阐发而沦为“政治化约论”[6]P258。而这些批判也恰恰证明了赵岐在注《孟》过程中对“以意逆志”做法的坚持。
赵岐在《孟子章句》的章指使用和篇章设置上对“以意逆志”的贯彻,体现了孟子诗学在汉代四家诗中影响的深远,其影响突破了诗学层面,而且广布至经、子典籍的注解与阐释。
参考文献:
[1]周广业.孟子四考.(影印复旦图书馆藏清乾隆六十年省吾庐刻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173-183.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朱熹著,蔡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胡毓寰.孟子注释之三部名作的批评[J].申报月刊,1934,3(12):85.
作者简介:李华(1982-),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