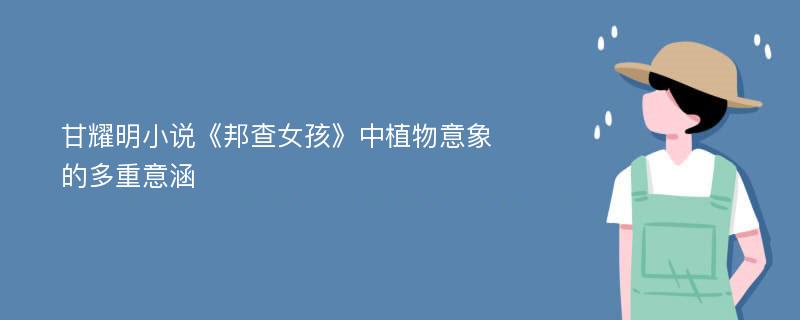
(集美大学,福建厦门361021)
摘要:植物始终和人构成着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甘耀明在小说《邦查女孩》创作中继承中国文学善用植物意象传达思想情怀的传统,将多种呈现形态的植物意向灵活运用在作品当中,并赋予其层层深意,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女性意识、家族意识的重视与呼唤,从中凸显出的生态意识也警示我们在工业化时代仍应崇敬自然。
关键词:甘耀明;邦查女孩;台湾后乡土;植物意象;自然
《邦查女孩》[1],是甘耀明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写实与魔幻结合的描写手法,充沛洋洒的想象力、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自然知识,描写了一段发生在大山深处、人类森林家园里的故事。细读作品,不难发现,原始而又神秘的森林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在原始森林中,数量繁多的植物也自然构成了作者描写和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植物和人构成的一种和谐共存关系,使得人类对植物有着本能的亲近,特别是各呈异姿的花朵,每每被人赋予各种深层的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甘耀明《邦查女孩》中植物意象的分析,探寻甘耀明在其台湾后乡土小说的书写中所要传达的某种生命意味与独特情怀。
一、植物意象的多种呈现形态
在文学作品中,植物意象历来被文人所青睐。从中国文学之源的《诗》、《骚》,到现代白话诗和现代小说。《国风·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2]即是以长短不齐的荇菜来形象地传达少女的春心萌动,少年的风流情深。“荇菜”在诗中也作为“君子”寻求配偶的美好象征物。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则留下“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3]以“木兰”和“秋菊”的植物意象表达诗人高洁的情操。到了清代,郑板桥一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4]又让我们领略到岩竹历经磨难却又坚劲挺拔的高风亮节与铮铮傲骨……
甘耀明的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善用花木的文学传统,却又能别出心裁。甘耀明于2003年深入到花莲县凤林镇的摩里沙卡体验生活。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又一力作---《邦查女孩》。正是由于甘耀明有了传统乡村生活的体验,加之他的《邦查女孩》又是以原始森林为小说的主要背景,内容大多基于伐木、登山等等,使得其小说中植物意象大量呈现。据不完全统计,《邦查女孩》中所提及的草本类植物、树木约有100种,如荔枝树、面包树、苦楝花、榄仁树、核桃树、茄冬树、榕树、马先嵩、玉山蓟、瓶尔小草、牛筋草、苹果花等等,作者倾注众多笔墨绝非偶然,透过植物意象,应当可以看出他所要传达的某种思想或象征意涵。
二、植物意象的主要寓意及对人物的指涉
(一)松柏/木荷——生命意识的象征
《邦查女孩》中常出现一类植物,它们以松柏、木荷、早田氏香叶草、核桃树、竹林等一系列植物为代表,其共同特点是身处逆境却经久不衰,渺小无依,却傲然挺立。
最有代表性的是圆柏。小说描写了圆柏树,在万物飘摇、大地落白的冬季,在强风直击、暴雪骤虐的六顺山山顶处,它迎来了自己两千岁的生日。“可是圆柏不图安稳,常在迎风处或山巅出现,挣扎求存,树干给千万次的风雪扭成旋转的姿态。飞雪越强,寒风够辣,圆柏绝对以身相迎,常在背风面结成凝固飞旗般的冰晶——雾凇。”这是生命赋予的荣耀啊,用坚劲的魄力去傲视四海八方的悲凉与磨难,呐喊在孤独、黑暗、绝望的边境,仍然义无反顾承担起“生”的重任,这种“生”是烙印在魂魄里的,是它自存在那一刻起就拥有、并且值得用尽全力去捍卫的。
如果说坚守在皑皑白雪下的圆柏算是勇者,那么挺立在熊熊大火中的木荷就是战士。在一场蔓及五十几公顷的森林大火后,火车辗转了八个峭壁弯,终于来到了空余树木骨架的火场。在火场的棱线边,古阿霞惊奇地发现了木荷的身影。即使树干已是“瘦长湮郁”,但仍然无法阻挡木荷抽卷新芽的进程。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用钢浇铁铸的勇气去修复节节疤疤的生命,如何在废墟之上昂起头颅自我重建,才能做到矗立在焦黑战场仍然生机窜苗。
还有深藏在花莲礼堂花圃角落发芽壮大的核桃树,向阳的崩塌地中未被台风驯服的早田氏香叶草……这里的世界不存在蹂躏与毁灭,只有平静中充斥的神圣,它们都代表了蕴藏在原始生命强力中的积极生命意识,隐含着作者的情感积淀、生命体验和悲悯情怀。
小说叙述的人物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的台湾,二战残留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摩里沙卡,这个以林业为主、带有封闭色彩的小山城,还未摆脱贫困状态。不仅如此,大面积砍伐还让这儿逐渐失去生态平衡。不便的交通迫使孩子上学需乘坐危险的“流笼”[5],男人们依靠危险的高空作业和运送原木为生,疾病无处不在,文化、教育普及程度极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活着”成了一件用概率衡量的事情。“双傻”中的赵柏青因为落桥而亡,捆木工滑落到铁轨撞击身亡,野生动物生活遭遇困境……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死亡作为这个林场一以贯之的主题。尽管如此,每一场伤痛过后,铭记着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固有轨迹上生活,代代延续。因此甘耀明笔下的林场生活虽然处处充满个性理想消耗殆尽的破裂声,但同时呈现出这片山林里人们的“挣扎与追求,欢乐与疼痛”的碰撞,这种有血有肉的斗争顷刻间化为命运协奏的交响曲,如松柏、木荷一样,在千锤万击中越挫越勇,沉稳而激昂。
(二)
1.水晶兰/山棕花——女性意识的觉醒
秋天,是黑熊开始准备觅食御冬的季节,雨后的森林湿漉漉的,水晶兰注定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隅。它虽出自腐殖土,但却通体透明,作者这样描述它:“活脱脱像是凿下月光般锻造的器皿”,潮湿阴暗的地带并没有使它沾染上阴郁昏沉的浊气,反而是洁白晶透,幽香清远,用特有的白色光亮悦人心目,引人伫足欣赏。有人说它似冰雕,像蘑菇,这些比喻放在它身上都太过俗气,用“如玉清莹,如梦隽永”来赞美它再适合不过。
生长在森林深处的山棕花则选择让窸窣落下的橘黄花朵们顺溪而下,用其特有的芬芳穿透林子,浓郁且谦冲,高调又清丽。年幼的古阿霞洗了山棕的叶子澡,竟然不哭不闹也懂得该笑了,让人获得温柔的抚慰。同时,她也善于用尖锐的山棕叶抵抗外扰、保护自己。柔是她温柔脱俗的抚慰,刚是她丰满坚硬的叶羽,顾盼生辉间又透露出琉璃般的光辉与泼辣,刚柔并济间折射出特有的中国女性之美。
作品中这三种植物主要喻指美好、纯洁的女子气质和人格形象,包含坚韧、勇敢、独立等一切的美,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精神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古阿霞、素芳姨等女性身上。
古阿霞是一位充满“正能量”、敢于挑战、经历不凡的少女。作品一开头,她就勇敢地抓住机会和帕吉鲁一起远走高飞了。深入“摩里沙卡”后,她又努力摆脱充满苦难、寄人篱下的困境。接着,她为了改变孩子们坐“流笼”上学的现状,主动和帕吉鲁一起筹备山顶学校复学之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得以恢复。作品还用生动简洁的叙述性语言描述了另一位女性——素芳姨,她是帕吉鲁的母亲,顽强的性格、坚强的品质让她坚持攀越高山峻岭的梦想,即使在失败之际,也不惜冒险独自登峰。不仅如此,这两位女性都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对待傲慢偏见的眼光和男性的疯狂示好,正如水晶兰和山棕花一样,用芬芳对待周遭的美好与欣赏,不流俗、不谄媚,用反抗对待环境的邪恶与黑暗,捍卫着女性独立的人格。
2.高山蔷薇/虎杖花——女性独立精神的丧失
与之相反,作者却分别用“娇惹”、“惹人嫌”来形容高山蔷薇与虎杖花,它们或是因为经受不住低温的考验而蜗居高处,或是必须借助他物挡风遮雨方可生存,也具有隐喻意义。作品中不少女性处于下层阶级,生活状况堪忧,便将男人作为生活下去的支柱,一味顺从,导致情感世界空虚靡乱。古阿霞的母亲与参加过越战的美国父亲赫尔曼认识后生下了古阿霞,数年后母女二人即被抛弃,她常被母亲关在房里玩,凌晨才能看见花枝招展的妈妈回家,床是邪恶的化身,它带给大人淫念的同时也让古阿霞的童年获得无尽的噩梦。生活总是不如诗,这些看似淫乱的妇女无人不有难言的痛楚和伤痛,为了生存不惜僭越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在她们看来,苟且活下去远比遵从三从四德、追寻独立人格来得现实。她们就像蔷薇与虎杖花一样,在趋附中生存,成为强势者的附庸。
(三)森林——家族意识的延续
咒谶森林里生长着六百零五棵可列为世界奇观的扁柏,其中一半都已达千年以上。它们的种子在暴雨中洒落,通常在母树倒下后,落在母树身上的种子才得以生长,生根发芽,母树则化作隆起的树根代代存在下去。几代树重叠在一起,盘根处有时会形成类似骨骼切面的美景。森林中不仅“生”会代代相传,有时连死亡也和周围的一切息息相关。人人都知晓动物能够传递讯息:比如海豚会自发性搁在海滩死去,生病的裸鼢鼠会呆在垃圾堆里直到死,这样就杜绝了染病给同伴的可能性……但鲜为人知的是,植物间也存在传递讯息的方式。原来,当某棵树被砍掉之后,死亡讯息就会通过根系在森林中传递,不为人知的悲伤弥漫开后,就会有其他树开始通过加速体内病菌腐败,以吸引雷电、引发大火等方式“自杀”。这是一种同根同源的归属,如此肃穆、壮美、神秘莫测,时间在这里无路可走,于是一棵树、一片林的情感,便积淀作密密麻麻的年轮,永垂不朽。
血脉亲情和家族意识不仅在植物中存在,更是人类的本能。生死轮回在血浓于水的生命间,一个家族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由弱到强,这是值得敬畏的文化伦理传统。当过去所积攒下的经验和法则渐渐失效,当传统礼法和乡土社会正在一点一滴面临不可避免的崩坏,我们仍然可以在细细品读文本之余,窥望缝隙中点滴温暖的慰藉以及令人震撼的自然力量。
《邦查女孩》中反复出现的“森林”这一意象,象征理想家族意识的延续,它们盘根错节,命运相连,它们仿佛无所不知的神明,默默见证着这里的沧海桑田,在小说中直接代表了菊港山庄世代延续的团结力,这些村民的一生都兜转在生活的迷宫中,迷茫、困顿、愚昧、悲痛从未离开他们,但他们不曾丧失“归属感”,这是隐隐生长在飘荡灵魂深处的东西,无人言说,无需交流,却就一直在那里。
在林场上,“穷光蛋们”排队赚钱,危险随时都在,每逢有伤员出现,即使存活的希望渺茫,其他工友或青壮年都会搬动伤员下山;如果有人死去,大家也会为死者上香、烧纸钱,让那个夜晚充满芬芳、光明与温暖,他们照样喝酒聊天,也只为用互动来掩饰充满压抑的悲伤,因为每一个生命的流逝都值得尊敬和留恋。此外,作者还善于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用神话故事点缀整部作品,这些故事大多关于鬼神与死亡、迷离的家族传说等,以此来追寻主体的存在感或认同感。作者试图捏造出一个怪诞的时代或故事情境来正视血浓于水的亲情,把家族意识蕴含在对时间和死亡的命题中。试想,有多少乡亲在垂垂老矣之时,迈着蹒跚的脚步踏上前往过去的征途,卧在直插云天的大树下,吮吸森林的气息与馥郁的花草香,顷刻间所有记忆浮上心头,人生的起起落落,家族的兴衰变化刹那间尽收眼底,便又将家训和希望寄托给大树,馈赠给子孙后代。
“乡土范畴不仅实指具体的地方、某个社会空间,也推廓为提供归属感、认同感的有界地域或植基于对地方的经验或想像,而其中对于家族、地方、民族、种族、本土方言、信仰习俗等的认同,即可填补‘乡土’空间的隐喻与指涉。”[6]更高层面上,这种家族意识也代表着:在多元化的台湾,原住民、外省人、外国人的大融合让大家族日益兴旺,薪火相传,这种力量是深深激荡在中华儿女血液之中的,代表着血缘认归与祖先崇拜心理的继承,是人们反思过去,理解现在和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小说中的森林与家园,都是作者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那个心灵家园的映射,是他在寻找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归属和寄托,向读者展现一个荒诞、颓废之外的温暖与力量。
三、生态意识的凸显
人类文明就是一部不断认识与征服自然的历史,这似乎从人类诞生起就成为不容置疑的命题。1970年代的台湾经济飞跃增长,“十大建设”等工业热潮火热进行,牺牲山林也成了工业生产的必经之路。在许多人提出“返璞归真”、“重归自然”的今天,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早已抢先一步,与自然为伍,把自然渗透在生活、乃至生命的方方面面。
“难道值得用一座森林,换一间学校吗?”古阿霞在学校前途和森林命运间两难。“这没什么不好,要失去森林,才会记得森林的好。”帕吉鲁坦然的回答不由使人深觉遗憾和痛心。要青山绿水还是发展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否和谐共生,都是值得我们永恒思考的话题。在书中,作者将男主人公帕吉鲁作为自然的化身进行了回答。
这个患有失语症的男孩,在幼童时就能数清银杏叶子的数量,因落花流泪,与树对话,为树治病。他将树木视为亲人、看作朋友,最终他的命运也和树木联系在一起。小说在表现主人公对森林的热爱的同时,还表现出对一切生命的保护。在玉川旁,帕吉鲁为了拯救母鹿,巧妙设计“救生圈”,让黄狗入溪咬住水鹿上岸,随后与古阿霞一同帮助母鹿生产。“水鹿母子会找到河水的第一滴,在源头必然没有杀戮了”这一美好愿望也反映出对生灵万物的爱惜与尊重,他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呵护和关爱,自然界的生物,都拥有相同的价值。
梁鸿把甘耀明看作一位“孜孜不倦的挖掘者”:“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尚未觉醒,或者,遗忘太久的自己,让我们看到人的精神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他的这一世界包含了我们正在抛弃的自然和肉体,而它们,自然——森林、动物、植物,肉体——与自然相通的、一体化的肉身,曾经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和灵性,我们的思维与情感包含着它们的元素和形式。越来越工业化科技化的文明正试图把这些元素驱逐出去,因此,人类孤独、绝望,充满着惶然和惊恐。毫无疑问,甘耀明的小说试图让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重新回到那些元素之中,他试图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元素下人的存在的形态。”[7]帕吉鲁就像一只充满灵性的飞鸟,在现代文明和那个有着独特气息、秘密语言的奇幻世界间来回穿梭,一头是他的亲情、爱情和乡土,另一头是他的使命、自由和灵魂,在作者别出心裁的构思下,两个看似相互对立的世界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和自然的转换。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棵树可能正在演绎这天地之间的轮回流转,人类于宇宙而言也只是沧海一粟,善待生命,从容地活着,也许这就是作者要传达的。他通过这些小窗口,让身处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我们,在傲慢改造大自然的同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为我们开辟另一片家园,寻求生命的真谛。
参考文献
[1]甘耀明:《邦查女孩》,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2]王秀梅:《诗经》,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
[3]林佳骊:《楚辞》,中华书局,2010年6月,第1版。
[4]卞孝萱:《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6月,第1版。
[5]一种连接在滑轮上的木箱,用于承载人员物件。
[6]陈惠龄.乡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湾新乡土小说书写风貌[M].台北:万卷楼图书,2010:13.
[7]梁鸿.自然、肉身与现代文明的处境——甘耀明小说读札[N].文艺报,2017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