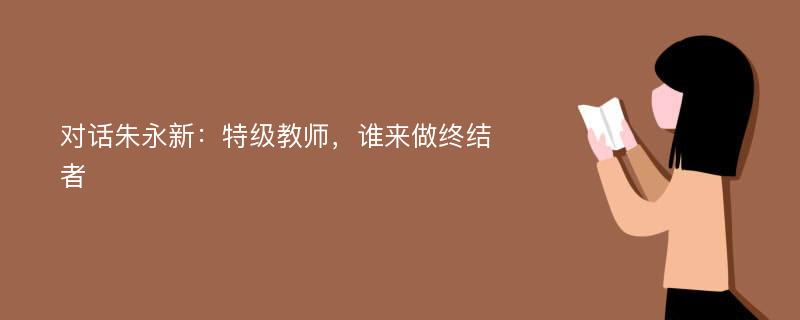
朱永新姜广平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谈过很多问题了,现在将话题转移到特级教师上如何?
朱永新(以下简称朱):好啊!这个问题在你《北京文学》上发表《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时我就想和你讨论一番了。
姜:关于名师的培养机制,其实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是:大多数名师的成长过程往往并不是那么顺利。社会环境或教育环境给予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大多数名师是在一种自发状态下,凭自身的强硬打拼浮出水面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管理者不能创设一种优良的教育环境,促使名师们或准名师们迅速成长呢?
朱:名师的成长需要环境,尤其是一种宽容的环境,理解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想的环境是由一个名校长来提供的。校长就是一个学校的导演。舞台的搭建,气氛的营造,灯光的设计,都需要校长去努力。他把老师们推上舞台,成为学校的主角,而不是自己粉墨登场充当主角。这样教师就能比较好地成长起来。现在在很多学校,主角都是校长。教师是很难超越校长的,甚至教师是为校长服务的,因此,绝大部分的名教师无非是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在校长的帮助下,从学校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的。但是也有一些教师,就像你说的,是靠自己的底气,靠自己的强硬,靠自己的坚韧打拼出来的。很多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或者说是在外面先建立影响,然后逐步在本地区或在本校有影响的。
姜:对一个庞大的教育体制而言,名师之名,现在倒出现了某种反讽的现象。因为名师之名,往往大都在于自身的个性与才气,是名师们的自身努力成就了名师本身。如果没有这一点品质,名师竟然就不会再出现。即使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名师,也往往昙花一现。我就想,难道教育真的有某种不能承受之重吗?
朱:这一个问题与前一个有联系。真正的名师应该在学生心中很伟大的。名师之名不是靠宣传与吹捧出来的,这样的名师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我们现在的名师,在现在的体制下往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他一方面要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要适应现实的环境,否则,他还没有出土,就会被冻僵了。因此,名师本身的个性与才气,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了他的社会适应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甚至对付考试的技巧与技能。他一方面用思想征服这个世界,同时,还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总体上讲,我们的环境,还有待于改善。还应该为名师的成长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
姜: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一个人最大的发展境界,是能够有最多的闲暇时间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大多数教师认为教育并不是自己很想做的事,因而都做得非常勉强。忙碌的教师生涯,使教师们对教育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对教师职业的厌倦情绪很大,陷在一些事务性的圈子里,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你觉得能将教育做好吗?我们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朱:我经常说,教师的职业是用整个的人生来做的。他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教育的生活。他读书、看新闻,与朋友交往,甚至于自己做插花及与教育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可能而且应该是教育的元素。譬如说你姜广平是一个作家,但对你的学生来说,你首先是一个教师而不是一个作家。但是你的作家身份与生活及体验,你会带到教育中去。你会让孩子们发现一个多彩的你。现在的教师职业的厌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生活的单一。教育的另外一个使命是人生体验的教育。教师不是简单地把知识给孩子,他应该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经历全部交给他的孩子们。所以,一个多元的教师,一个兴趣广泛的教师,一个热爱生活的教师,才能真正唤起陔子们热爱生活的情趣,才会形成孩子们多元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把自己仅仅作为分数的奴隶,走应试的独木桥。
姜:所以,我一直认为,教师沦为“教育警察”,甚至是扼杀学生个性的“刽子手”,也是教育管理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教育民主所导致的后果。这里可能也与教师的追求有关。教师的情商可能不是很好。从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角度说,我觉得,一个教师必须具备优质的情商。说穿了,教师自身也有一个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问题。往往是那些非智力因素特别好的教师,越是能体会到教育民主的浓郁,同样也能给予教育同行与教育对象以真诚的尊重。
朱: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的教师与一个平庸的教师,差别不在智商与智力。我也经常讲,人与人,在智商上的差别是有限的。特别聪明的人与智商特别高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智力背景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他们的差别往往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我曾与我的老师燕国材及现在在教育部的袁振国老师写过一本《非智力因素与学习》的书,我们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公式,这一个公式其实就是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函数关系的。智力因素是相对不变或基本不变的。谁的成功率大,取决于谁的非智力因素好。因此,教师同样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非智力因素或者你所讲的情商。
姜:因此,我对名师们,特别是特级教师这一群体不是很看好,既过于庞大,产生机制也很值得怀疑。这一队伍中的人,动机性、目的性,可能都不那么纯粹。对教育的虔诚度同样是令人怀疑的。
朱: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论证可能会伤害我们很多特级教师。总体上来说,这批教师,还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因为我们事实上很难能考量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包括对教育的虔诚度。我们只能通过外显的行为和外在的成果来评价一个教师。总体上来说,特级教师教学的成绩是好的,教学的成果是多的。当然,特级教师之间也是很不平衡的。有一些是有思想的,可能有些就显得不够,而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有些是有追求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也有一些人就可能不是那么高尚。我们总体上应该宽容他们理解他们。当然,现在特级教师的产生机制的确是有问题,我曾经也讲过,特级教师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级教师也没有什么高明。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每一个校长,每一个学生,心里都有一杆秤,什么是好学校,谁是好老师。如果评特级教师,更多地听听学生们的意见,听听家长们的意见,可能就会客观点。另外,特级教师也完全可以不要评,因为,任何一个教师,他的精神境界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评估来影响他的一生的。给一个教师一个帽子,让他永远戴一辈子,很可能使一个教师失去了成长的动力。
姜:但从教师形成个人特色、个人风格角度来讲,也还是非常不易的。你觉得要怎么样做才能使一个教师甚至一个特级教师真正达到大师水准呢?
朱: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参加我们的新教育实验。最基本的做法就应该是读书。因为我觉得读书不仅仅是教育中的一件大事。我是行政官员,你做作家,任何一个领域要做得非常优秀,都必须要读书。书是人类几千年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与积淀。你如果不读书,不与大师对话,很多事情你必须从头开始,你就得面临着你的前辈甚至前辈的前辈他们的那种起点。
姜:除了读书呢?
朱:那就是思考。我们提倡写教育日记,也是一种反思考的过程。日记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内核正是反思。反思的前提是行动,只有在行动中,他才能进行反思。他会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做成了,为什么做不成了,从而在第二天或此后的工作中体现出自己的思考来。袁伟民曾经跟我讲过,他当时训练女排时,对郎平的要求就是每天要写训练日记。
姜:噢,是这样的。
朱:今天我见到的徐向洋(择差教育创始人——姜广平注),他要求他学校的教师每天都要写教育日记。这完全是与我们的新教育实验不谋而合的。
姜: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我自己来了。我没有写教育日记,但我写的是教后感或课后感。每一节课后都写。当时,兴化中学的特级教师柳印生对我说过,姜老师你不需要做其他什么事,只要将自己的课堂实录下来,然后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进行推敲,长期做下去,你就非常成功了。
朱:的确是这么回事。反思肯定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最好的途径。
姜:这里面也涉及到个人修养的问题,教育日记同样是一种道德长跑。这里我又想到特级教师们能走多远的问题了。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特级教师们是能走得很远走得很高的。可惜我们的一些特级教师起初的出发点便值得怀疑,最后只能为一己之私利而无法长高。南京某校招聘教师,24名特级教师落马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损耗与浪费啊!
朱:这还是回到一句老话,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人。你要做一个好老师,也首先要做人。
姜:我觉得现在很多特级教师更缺乏人格良知与道德良知。
朱:关于人格良知与道德良知的形成,事实上又回到了读书上面。我经常说,学历的高度不等于道德的高度。但这里面的情形又比较复杂。譬如,一个文盲老太,她更多的是一种人际道德的高尚与否,她很可能做到舍我助人,但她很难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她看不见的世界。
姜:是啊。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些特级教师成长起来了,但恰恰正是这些人,反过来却要压制、打击、甚至排挤新的成长起来的力量。这在教育场景中似乎并不鲜见啊!
朱:道德的情景与读书是相互联系的。当然,你所说及的一些现象,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包括特级教师们,大多是在一种缺少人文关怀与道德境界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鼓励大家善的追求。人不完全是教育的产物,但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道德风尚,会规范着社会当中的一些群体。你所说的情形,其实并不只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在相当大的层面上,都有着这样的倾向。这些人其实就是将个人的发展或个人的快乐,建筑在践踏别人或者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这不是我们应该鼓励与提倡的。对一种真正的实践道德的提倡、建立,在我们的教育中,要进一步强化。
姜:我记得你也谈过高教界的情形,你说你与海派京派都能相处好,反而,京派与海派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我总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相容?我们基础教育领域里面,可能因为生存的问题,这方面可能表现得激烈一点。当然,在我这里,我觉得我与你比较一致的是,我非常能够容人。如你所谓的,善待自己,悦纳他人。但更多的情形却是令人遗憾的。很多人,特别是名人,对别人的接受与认可是很有限度的。所以,我总觉得,从国家体制上讲,像这样的名师是不是还有培养的必要?某种机制我觉得还是打破的好。这样反倒更能利于人的成长。
朱:其实,同样是特级教师,其份量是不一样的。我不主张给中学教师一个终生的称号。在实践中,国外的大学,只有终身教授是终生的,其他都不是终生的。但还要有相当长时期内的事实与实绩的证明。
姜:这就像我们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它是对一个作家毕生文学成就的认定。特级教师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它在我们的教育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在科学的春天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到来时,一个民族需要巨人并能产生巨人的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但现在,我们清醒地看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需要是一回事,但一个群体能否达到这样的需求水平是另一回事。更何况,现在的特级教师,小学的与中学的层次肯定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其情形又是非常复杂的。说实在的,教育中很多厚重的东西,是要到了一大把年纪才能有所把握与有所感悟的。《江苏教育》搞的新生代专题,参与者中的小学教师,都非常年轻,我曾与他们作过交谈,觉得有着很深的人文底蕴与很深刻的教育思想的特级,实在太少了。这样的教师竟然是小学中的佼佼者,我觉得小学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当然,像窦桂梅这样的小学特级可能也是少而又少的。另一方面,地区之间的差异就更大。譬如说,北京的曹阳,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教师,可是,他现在还被关在特级的门外。但这样的教师,如果放在东北与西北地区,可能早就是特级了。当然,曹阳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在中国还主要进行应试教育的今天,他有着他的弱点。所以,我如果再说一句偏激的话还请你理解:现在的特级教师,确实如我所说,已没有多少人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了。无论是学术高度,还是精神引领,特级教师这一个群体可能已很少人能在这方面称为大师了。怀有一种教育理想与人文精神的人则更少。很多特级教师,其实仍然只是文化侏儒。另有一点,特级教师在评选中,似乎还存在着学科的偏向,语文特级特别多,其他学科特别少。但深具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多。我觉得这样的评选机制应该停止了。
朱:在某种程度上,越评质量越差了。最拔尖的都被选出来后,就只能是矮子里面选将军。为什么一定要将这种制度保持下去呢?我觉得是应该废弃的。不过,我主张每一年选一些优秀教师,作为年度优秀,进行奖励,对他这一年的工作进行肯定。
姜:对对对。就像有关媒体搞出的年度人物。
朱:是啊。就像我在《南风窗》得到的这一个称号(朱永新获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它就是年度性的。明年如果我做得不好,那肯定就不会再被评上。
姜:我相信你明年会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这些普通教师既对你有着某种期待,但也有着某种压力。这种压力也是一种推动力。你不能让我们……
朱:是啊,我不能让你们失望。哈哈……
姜:这说穿了其实是一种压力。
朱:的确是这样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属于整个新教育,属于整个教育在线。说到底,这些年来,我也在成长。
姜:朱老师谦虚了。但我接受你的这个观点。我们都在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连你到了这样的境界都还在成长,我于是就想到,人的成长其实是不可限量的。如果哪一天固步自封,就一定会退步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总觉得自己到了这个位置上,便什么也不要追求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其实,新生代浮出水面之后,这一代人对教育的发言,特级教师群体应该感到一种压力。这些人大有超越特级教师的可能,个别佼佼者,他们的成就可能是很多特级教师一辈子都难以超越的了。
朱:是这样的。
姜:还有一种情形,现在很多特级,是在等着称号。一旦有了,便孔雀东南飞了。将自己作为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希求在教育市场上卖出个好价钱。教育走向市场的今天,我对这点不反感,但真正因为当地没有了自己的教育空间而想寻求一个理想的教育空间,这样的人可能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因为利益的驱动。如果特级教师们都只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加入行走一族,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教育的悲哀。这样的特级教师,你期求他能长高,可能也是一种空想。
说到利益的驱动,我又想到了教育科研问题,现在教师们的科研其实是非常紊乱的,我觉得这些方面,特级们也有责任。他们没有把这些工作纳入自己的工作范畴,对其他教师的指导也近乎于零。
朱: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们的教师写写教育随笔那一类东西。教师的这种写作是一种更加鲜活的灵动的实践的科研,是记录自己的教育故事,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是自己的烦恼的反思性的写实性的科研。我不主张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用论文来评价他们。我在新教育实验里,师生共写随笔,就是想用一种新的科研样式来取代传统的科研论文。事实上对很多教师来说,论文,尤其是空洞的论文,理论堆积的论文,除了抄袭拼凑,没有其他的办法。
姜:除了这点还不够,你谈到过,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理想教师,他应该非常关注社会,非常关注人类命运,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特级教师们更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很危险,大多数教师并没有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人格分裂者更多。在人格的困境中挣扎尚属于一种好的现象,程度重的则是心理上有障碍,我觉得让这样的教师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