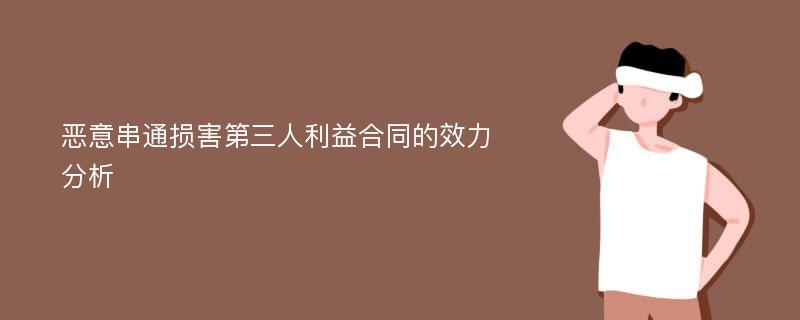
论文摘要
合同又称契约,是引起两个以上当事人之间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的双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具有相对性,一般而言,合同内容只涉及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有一些合同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引起了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主体的法益变化,这就是所谓涉他合同。民法的“禁止权利滥用”基本理念,在合同领域即可表述为“合同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如果当事人双方通过法律行为签订了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法律首先应当对这种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评价,这是进一步解决利益冲突的逻辑起点。因此,就必须应用民法中法律行为理论对此种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分析,进而平衡各方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由此可见,第三人利益已为此无效合同制度所保护,法律不承认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在实务中,合同当事人利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很多,一味地否定该合同的效力有时并不符合特定第三人的期待利益,立法所设定的目标并没有完全符合利益损害方的利益诉求。简单地否定合同效力的方式能否完成保护第三人利益的重任,我国相关法律规范提供了哪些救济方式和途径,是本文着重思考的问题。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立法涉及到了保护国家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该合同无效。我国法律用了最为严厉的字眼,否定了恶意串通合同的效力。不难看出,这里的立法规定,采取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用社会公共利益的天平来衡量合同订立双方的意思表示。毋庸置疑,这种立法方式惩罚了订立恶意串通合同当事人双方,使其期待的非法利益不能实现,切实地维护了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见,绝对无效的保护方式是适应国家利益保护需求的。但若仅仅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绝度无效的利益保护方式就显得过于僵硬了。同时,恶意串通情形下可能存在某些真实的意思表示,倘若仅仅因为合同的某些部分存在恶意串通就全盘否定整个合同的效力,似乎并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尽量促使合同有效”的立法初衷。观察《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且追缴财产、返还财产给第三人”的规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国家、第三人、合同效力的概念界定不清晰;主观要件证明难度大;合同效力规定过于笼统。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在虚伪表示领域立法的比较可知,首先,各国的规定较为一致,法条中均用“通谋(同谋)”来界定恶意。“通谋”强调是对事实的知悉,采用的是观念主义立法理念,故而虚伪表示的主观要件并不限定必须是故意,这样的立法方式大大扩展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其次,否定虚伪表示行为订立合同的效力,但不否定虚伪表示行为下被隐匿真实表示的效力,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也是我们应当借鉴的。第三,虚伪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被赋予了选择权,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对第三人的救济。同时,不揣学识的浅薄和疏漏,在借鉴大陆法系意思表示瑕疵理论及英美法系不可执行合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引入意思表示瑕疵、区分特定第三人与不特定第三人、给予形成权救济的立法建议。摒弃恶意串通的立法方式,明确第三人利益是特定第三人利益,虚伪表示主观要件上不再强调故意,细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