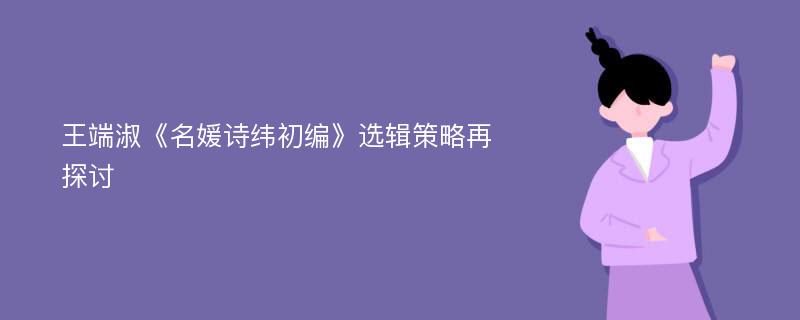
摘要:明末才女王端淑所编《名媛诗纬初编》为现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一窥明代女性诗文主张的重要文本。但学者们多挟今人观点、从性别角度阐释此诗集,对端淑本人的自白、评点、选辑策略缺少切实解读,从而对其存人、存史的初衷与用心认识不够。重读《名媛诗纬初编》,将其还归于当日语境之下,或可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女性创作与选政之实情。
关键词: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女性选政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5-0010-02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在数量上远迈前朝的女性诗人,她们写诗填词、作文论艺,以文字为生、以文字交友、以文字打发穷愁无聊的生活。而其间学殖优厚者,如方维仪、季娴、沈宜修、柳如是、王端淑等,甚至参与、主持编选、刊刻女性诗文集,担当起操练选政的大任,以自己的标准建构女性历史与文学的谱系。
以女性身份编选女性诗文集,最著者当推王端淑。王端淑(1621—1706),字玉映,号映然子,又号青芜子,山阴人。明末名士王思任次女,丁圣肇妻。其父尝有“身有八男,不易一女”[1](P19)之言,陈维崧《妇人集》下按语说“山阴王家郎,俱有凤毛,季翁情钟贤女,遂损誉儿之癖”[2],然论者仍多引端淑之父言为端淑才高之表征。端淑一生著述宏富,成果斐然。作有《吟红集》、《留箧集》、《恒心集》、《玉映堂集》、《史愚》等,辑有《历代帝王后妃考》,编选历代妇女诗文成《名媛诗纬》和《名媛文纬》。明朝覆亡后,端淑与夫颠沛流离,“初得徐文长青藤书屋居之,继又寓武林之吴山,与四方名流相唱和”[3]。
《名媛诗纬初编》现存四十二卷,选汉魏以迄明清八百余名女性的两千多首诗词。除在前人基础上新近补辑少量前朝女性诗作外,主要集中于有明及清初这一时段的女性作品。选编过程自己卯年冬十月,迄甲辰年秋九月(1639-1664),历时26年:无论从所历时间还是从所成卷帙上,都较其他女性编选者所编女性诗文集更显恒心与伟力。
《名媛诗纬初编》得到了同时代诸多男性文人的推崇与赞赏,他们纷纷为之作序留跋。钱谦益的序言中,对本朝男性文人辑刊女性诗文集评价特低,讥讪说“本朝闺秀篇章,每多撰集。繁芿採撷,昔由章句竖儒;孟浪品题,近出屠沽俗子”[4],从而对女性操女性诗文之选政寄寓较大期望。许兆祥、孟称舜的序跋则因《名媛诗纬初编》的成稿“吾愧吾须眉”,并借与时俗表彰女性作诗文相同的流行语调说“昔谢戏象山云,自机云抗逊之死,天地灵异之气,不钟於男子而钟於妇人。盖不独为陆氏一家言也。吾於玉映亦由绎乎斯语”、“自抗逊机云之没,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之妇人,吾於玉映氏亦云。”
事实上,王端淑在《名媛诗纬初编》凡例中於自己为何编选女性诗文集有非常清晰的告白,她说:
余素有操选之志,然恐以妇人评骘诸君子篇章,於谊未雅。以闺阁可否闺阁,举其正也。如桐城方仲贤选《宫闺诗史》,邗上季静媖选《闺秀初集》,松陵沈宛君《伊人思》,而后不多概见。予故谬操丹黄,以昭甚盛。
如此看来,“以闺阁可否闺阁”并非是其初衷。她其实自信有更大的能力,能够“评骘诸君子篇章”,在主流文化圈内一展才华,只是慑於社会规则“於谊未雅”,而不得不有所放弃:合盘托出自己退而求其次的尴尬。
现代学者孙康宜、闵定庆对《名媛诗纬初编》有所探讨,均着眼于王端淑选辑的性别视角,代表了多数人对女性操练选政的看法和对《名媛诗纬初编》本身的认识。编选者的女性身份为论者重视,乃在于选政比创作更能传达、凸显个人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创作中的女性“发声”已能为后来者追索不已,编选女性作品的女性文人,其评断高下优劣,为论者重视是否有鲜明的女性特色,亦是理之所趋。只是,王端淑本人“性嗜书史,工笔墨,不屑事女红,黛馀灯隙,吟咏不绝”[5],“读书自经史及阴符老庄内典稗官之书,无不浏览淹贯”[6],“博极全书,湛深理学,居然有儒者之风”,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全面熏陶,又直言编选女性诗文并非其初衷,“女性”於她,只是一个生理或者世俗身份,从她内在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而言,是“士人化”,或者说“文人化”了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高彦颐视她为“明末清初女文人的典型范例”,确为有见。而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既有文化传统的、专属于女性的文化传统,又确可堪斟酌。所谓“男性眼光”、“女性文学批评武器”,或许本来就是后人以自己的尺度标准衡量前人。当然,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有别有男性的体验与认知自是不可抹杀,但对于王端淑这样的女性文人来讲,已然能够跨越性别拘限而放眼於更广阔的空间。钱、许、孟等男性文人对于端淑的推崇,或许也正是着眼于这个层面。
王端淑编选评骘女性诗文,虽是囿于某些社会成规所做的退让屈服,但耗费如此大的心力,亦有深沉的寄托在其中。她在自序中说:“诗开源於窈窕,而采风於游女,其间贞淫异态,圣善兴思,则诗媛之关於世教人心如此。”并自解取名“诗纬”之因,乃在于“退处於纬之足以存经也”。其夫丁圣肇更是描述了她在兵燹播迁中“於《吟红》、《留箧》之暇,寝食一《诗纬》焉”的念念在兹、矢志不忘,乃是由于深刻认识到“馆阁实录,一代有一代之心史;鼓吹旗纛,一代有一代之作手。传之者有人,失之者无罪。至於闺中诸秀,内言不出,传之者谁耶,失之者谁耶?其传其失,谁之罪耶?”故而以“一代之情、一代之泪、一代之血”,“为一代之女流惜之”。
陈维崧《妇人集》曾说“玉映意气荦荦,尤长史学。??????今人但知其精於诗学,无有知其通於史学者。西河‘著书不让汉时史’之句,亦可为端淑小传。”[13]丁启光为端淑作序说“昔人云,具才学识三长者可以作史。故惟曹昭一人足与玉映比伦,今人罕见其俦。”钱谦益评价《名媛诗纬初编》“亦经亦史,又香又艳。”无不看重端淑及其所辑《名媛诗纬初编》的“史学”价值,恰与端淑及其夫的“有关世教人心”的“心史”相呼应。
本着存史的宗旨,王端淑在选录上自然有有别于“性别、艺术与纯美的特殊性”的原则与标准。她其实在凡例中说得相当清楚,即:
诗以人存。如一人而有专集,则选其诗之臧否;如一人止有一首半首存者,虽有瑕疵,亦必录之。盖存其人也。
“诗以人存”、“盖存其人也”,窃以为,是她编选这部卷帙浩繁的女性诗集的最终旨归。《名媛诗纬初编》的编排体例为现代论者措意,其实,仔细读来,与明代中期坊间流传的那些女性诗文集相比,并无太大差异,都是按照女性所属的社会阶层归类排序,亦有道德判断参与其中。倒是端淑为诗人及其作品所下的按语,有极鲜明的个人特色。很多时候,在有限的篇幅内,顾左右而言它,并无一语言及所选诗歌的艺术特色。
最可注意的是,端淑明言粗率鄙陋之诗乃不轻弃,只在女子诗歌多不赖保存而风流云散。端淑并不讳言大多数女子诗歌的艺术水准,甚至明确说出“古今以来,负虚名者代不乏人,何况簪珥”、“春秋责备,独恕簪珥”之类的话,对女性所处境地表现出相当的同情与理解。种种判断,见出端淑对于当代女性诗歌水平的清醒认知。粗豪、粗率、鄙俚、俚俗、纤鄙、不甚佳、学究、腐气等负面评价,并没有妨碍这些女性诗歌的入选。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意在存史、意在求全,昭然可见。至于遗集部分,更只有一些女子的名姓,并无诗作。关于为何无诗亦录其人,王端淑的解释是:
女子深处闺阁,惟女红酒食为事,内言不达于外,间有二三歌咏,秘藏笥箧,外人何能窥其元舆?故有失于丧乱者,有焚于祖龙者,有碍于腐板父兄者,有毁于不孝子孙者,种种孽境不堪枚举。遂使谢庭佳话变为衰草寒烟,可不增人扼腕乎?于是汇遗集姓氏以襄大观。
进一步见出其求全之意与补史遗阙之良苦用心。
作为女性诗人,端淑既有文人视野又有女性创作体验,对女性诗歌有自己的鲜明主张。除了上述较笼统的负面评价,她也有针对性地对女性创作极易陷入的困境提出了看法。大抵认为女性诗歌最大的弊端在于脂粉气,也要避忌绮怨之辞。端淑认为脂粉气源于女子凡性,也是沿习所致,其实是囿於身份识见而固定化的窄小眼界。
编辑《名媛诗纬初编》的绝大部分时间,集中在明亡以后,毛奇龄见“玉映以冻饥轻去其乡,随其外人丁君者,牵车出门,将栖迟道路而自衒其书画笔札以为活”,遂发出“悲闺中之在道”之感慨。而端淑在如此境遇下,几集一人之力,成宏富巨编,实属不易。她在其中投注了自己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借女性及其诗歌为大时代留下一份印记。而她本人,也因此成为明末清初女性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的重要代表。
作者简介:王茁(1980—),女,湖北十堰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江苏南京,210093)。
参考文献:
[1](清)陈维崧.妇人集[A].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Z].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同上.
[3](清)邓汉仪.诗观[A].四库禁毁书丛刊[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4](清)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M].清康熙间清音堂刻本.下文引文如不作特别说明,出处均同此.
[5](清)王端淑.映然子吟红集[M].清刻本.
[6](清)王士禄.燃脂集例[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