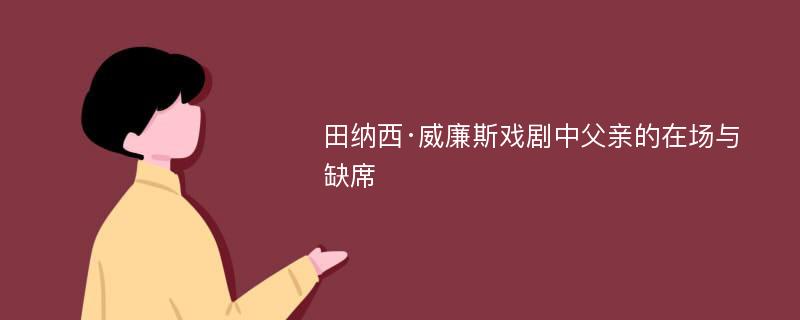
论文摘要
田纳西·威廉斯的不朽声誉和戏剧艺术成就主要基于四部作品:《玻璃动物园》(1944),《欲望号街车》(1947),《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以及《蜥蜴之夜》(1961)。在这四部获得评论界高度评价,同时又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百老汇戏剧中,父亲形象的在场或缺席深刻反映了剧作家本人的心理世界,同时折射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父亲的逃亡与温菲尔德一家的精神苦难象征了存在主义视野中上帝死后人类的生存状况;白兰琪阴魂不散的父亲则代表了一种有毒的文化遗产——体制化的基督教,最重要的日神幻境之一;要获得解脱似乎只能寄望于酒神的救赎。粗俗、盛气凌人、病入膏肓,同时又强大、仁慈的“大爹”代表的另一种救赎希望——美国实用主义;在酒神救赎的希望破灭之后,似乎只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才能消解勃力克内心哈姆雷特式的存在主义忧郁。《蜥蜴之夜》中老迈、赢弱的父亲形象的塑造则指向了新的结论:人类一次次踏上寻找父亲之旅,但最终总是发现这种探寻的虚妄;而他的敏感与尊严又使这位诗人父亲的生命本身成为歌颂人性的诗篇;他的倾听与表达的欲望预言了人类在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基石上重建理性信仰、实现救赎的希望。威廉斯的“塑性戏剧”富有表现主义特征。他这种对表现主义的广泛运用与其主题有关,他所着力表现的是西方文化内在的剧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类灵魂最脆弱、最柔软的部分所留下的伤痕。他的主人公常常是那个为内心的暴虐所“致瘫”或“致残”的现代人,他的戏剧情节常常隐喻着现代人对挣脱自我囚笼的希望与无望。威廉斯的戏剧体现出怀旧、逃避主义和原始主义的特征。他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原始主义倾向的最大贡献是他对性的处理。在他的剧场里,性几乎成了宗教,性似乎等于救赎。威廉斯戏剧的这种表现主义和原始主义特征,以及他创作中对性的迷恋,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它们更折射了西方世界对19世纪中叶以来剧烈的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共同反应:渎神、叛逆、革命、以及存在主义的绝望。隐喻的“弑父”仪式在家庭、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到处上演。每一个敏感的灵魂,在某一时刻,似乎都成了无情的或内省而内疚的“弑父者”。威廉斯的剧场里,父亲从来就不是主角,但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有些作品中,父亲并不在场,但是,他的缺席也被刻意制造成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作品之所以被美国大众广泛、热情地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他对父亲之在场或缺席的处理。它们反映了20世纪中叶美国大众与各种“家长”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对父子关系的处理激起了观众的共鸣。他的戏剧中所隐含的对父亲的评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轨迹。这道轨迹与美国文化的发展呼应、暗合。当然,从源头上看,威廉斯之迷恋于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与他在实际生活中和自己父亲之间的爱恨纠缠的关系不无联系。他舞台上的父亲并不是他的父亲康尼流斯·考芬·威廉斯的真实再现。但无论是差异还是相似,它们都是那个让剧作家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心生怨望的“老头”与威廉斯对他的不同观点的函数变化。父亲对他的影响,剧作家年轻时期对他的仇恨,以及他后期对“老头”的心理认同,无不介入了他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但是,于美国观众而言,于本论文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父亲观点的变化与他的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态度变化之间的互动。《玻璃动物园》中,父亲的缺席非常“显眼”。这种缺席同时释放了剧作家的两个潜意识欲望:弑父与对父亲的认同。《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桀骜不驯的形象,是威廉斯对父亲发出的“独立宣言”,炫耀他的成功,宣告他男性自我的确立。与充满阳刚与生命活力的斯坦利不同,这里的父亲是个死者,——再次表达了作者的弑父幻想。获得了充分经济保障与社会认同的威廉斯终于有勇气不但让父亲从舞台上缺席,而且“置其于死地”。然而,这两部作品的巨大成功并没有让他实现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尽管他继续刻意回避父亲,以此折磨、报复“老头”,在他的舞台上他却开始伸出他的和解之手。《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剧中的身体赢弱却仍然“强大”的“大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戏剧历史上最出色的父亲角色。坡立特父子之间的关爱纽带与康尼流斯·考芬·威廉斯及其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很大反差,但是它正反映了作者对互相关爱、支持、理解、滋养的父子关系的向往。《蜥蜴之夜》是威廉斯最后一部获得商业成功的百老汇戏剧,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精神虐待父亲的无穷悔恨,以及从这种无边悔恨中走出来的努力。这部作品中的父亲有时不无可笑、可怜、可悲之处,然而他的尊严永远伴着他,所有敏感的人对他肃然起敬。然而,田纳西·威廉斯对美国观众的魔力并不在于这些作品的自传成分。相反,我认为他的成功源于他的“非个人化”。许多评论家比较关注他的抒情性,语言表达力,和浪漫主义特征,我认为,他对观众的巨大“控制力”源于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深层关联。他的作品隐喻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灵魂深度的能唤起广泛共鸣的社会议题。父亲形象的在场或缺席帮助作品表达并深化了这种议题。《玻璃动物园》中父亲的缺席是一个有效的隐喻,指代上帝被尼采以及许多大思想家驱逐以后的人世生存状况。尼采对人类存在中非理性力量的发现触发了许多“创造性暴力”,这部戏剧是这种创造性暴力之一。它呈现了“父亲”缺席以后的分崩离析的存在主义式的世界场景。父亲的逃亡所导致的空虚、混乱与苦难,表达了对家庭这个人类最珍视的最后避难所的幻灭之感。在家庭里,爱遭受了失败,人无法超越卑贱的生存状态。父亲的缺席,还代表社会承诺的落空,特别是“美国梦”对人们的背弃,以及剧作家对宗教救赎力量的否定。《欲望号街车》中,女主角已经过世但阴魂不散的父亲代表一种有害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传统就是体制化的基督教,它是统治西方心灵的最重要的阿波罗幻境之一。白兰琪在斯坦利的地盘上极尽煽动、引诱之能事,导致了自身灾难性的毁灭。白兰琪的这种“蠢动”,只有当我们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强迫症时,它的悲剧性才能显现出来。她代表的是一种节节后退、衰弱无力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最后被迫退出以前,并不甘心于失败,它借白兰琪作最后的抗争,重申它的价值,它的高贵。这种传统正是白兰琪的父亲的文化遗产。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最后的胜利者是富有狄奥尼索斯特征的斯坦利,他代表了那种“神秘的原生性统一”。斯坦利与卢梭或者劳伦斯的高贵野蛮人不同,他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并不脆弱。他的酒神特征、他对性的迷恋是健康的,性赋予他力量,而不是置他于险境。这种自我肯定、自我赋予力量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与白兰琪的阿波罗式的自我否定形成了巨大反差。阿波罗式的无效然而有害的自我否定正是她已故父亲所留下的让她无法挣脱的有害遗产,是她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对父亲的正面描写,宣告了“王者归来”。这个救星般父亲的出现,反映了威廉斯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皈依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中帝国心理的膨胀。尽管“大爹”身患绝症,他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是个仁者。他的力量与仁慈将陷身于存在主义忧郁而不能自拔的儿子拯救了出来,同时让儿媳,那个在热铁皮屋顶上苦苦支撑的猫,安全地返回了至少暂时解除了火警的家。勃力克的忧郁与他对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的拒绝不但会将他自己带向毁灭,而且必然累及无辜的麦琪。他们需要一个救星。首先是麦琪,最后是勃力克,在“大爹”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救星的品质。作品将父亲塑造成一个宽容、睿智、仁慈和力量的化身,是威廉斯向美国价值(观)的最直白的致敬之作。在威廉斯和他的美国观众看来,只有这种价值观才可以拯救美丽却无法停止自毁的儿子(代表困于存在主义的焦虑而不能自拔的西方社会)。处于这个价值系统的核心位置的是实用主义,它的无可阻挡的魅力体现在“大爹”与麦琪身上。在长子的实利主义与次子(男主角)的浪漫主义之间,“大爹”选择了后者,代表了剧作家对实用主义的认同。这种实用主义,它不是浪漫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保护神。麦琪是剧中另一个——更为可爱的——实用主义的代言人,她是美国人对勃力克式的纯真与“大爹”式的成功这两种相互矛盾欲望的中和。“大爹”这个土生土长的非常有原创性与典型性的美国父亲形象在威廉斯舞台上的崛起,反映了剧作家对美国文化的感恩心理和20世纪50年代美帝国最终确立其西方领袖地位这一历史时期美国社会的心理变化。《蜥蜴之夜》标志着威廉斯从尼采式创造性破坏冲动向建设性思想交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首先清算了自我,清算了性救赎幻想、逃避主义和存在主义。该剧最初呈现的是一幅典型的存在主义场景:人间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自我是地狱。那个被囚的蜥蜴,似乎是失去了上帝照料的人类的卑贱生存处境的极好象征。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天使扇动翅膀的声音逐渐清晰可闻,人性显示它的天使品质。因为人对交流的欲望、人的交流的能力,使人在现世就有获得救赎的希望。在拒绝存在主义式绝望的同时,该剧放弃了对尼采式酒神救赎幻境的营造。尼采式酒神救赎在威廉斯的剧场内主要表现为性救赎。威廉斯是一个“性势利鬼”,“没有性爱,就无法获得救赎”之类的假“预言”此前一直回荡在他的舞台上。《蜥蜴之夜》摒弃了这种救赎公式。男女主角之间有长篇的思想交流,也有类似调情的唇枪舌剑,这种交流带来精神的相互取暖,以及对人性、对世界、对生活的新的体悟,但最终都没有导向两者的性的结合,打破了观众习惯的浪漫主义期待。剧中老迈虚弱的父亲形象也与此前的父亲形象完全不同。他自己也像那个被囚禁的蜥蜴一样,无助,卑贱。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威廉斯试图放弃对象征救赎的父亲的探寻,代之以对人性、人类互助与人类交往理性的信仰。《蜥蜴之夜》是对怀疑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温柔但坚决的正面冲撞和成功挑战。它预示了哈贝马斯们的修复人类理性大厦的努力。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当时还没有出炉,但该剧与交往理性理论的挑战对象——理性危机——与解决方案——以交往理性为人类新理性大厦的基石——是一致的。诺努,该剧中主要的父亲角色,不是《玻璃动物园》的父亲那样的背弃者;不像《欲望号街车》中的父亲那样,代表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化重负;但也不像代表美国实用主义的“大爹”那样,具有自苦难中救拔世人的力量。他的主要价值与扮演儿子(女儿)角色的夏农与汉娜的价值是一样的,是任何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固有的价值,这样的灵魂,它总是在表达,在倾听,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