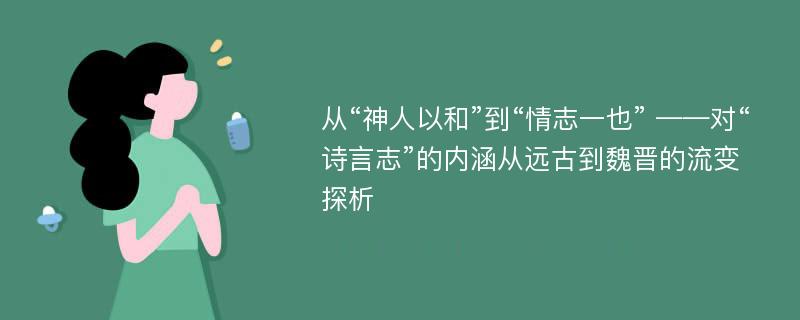
论文摘要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其发展脉络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尚书》时期、《诗经》时期和诗人时期。通过分析“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对于解答诗的源头、本质、功用等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尚书·尧典》所记载的“诗言志”是这一理论的开始,年代虽然不可考证,但是根据对整段话的理解,“志”应该指向“神人以和”,那么由此看来,诗应该就是表现先民集体宗教意识的咒语和祷文了,而做诗的人应是巫祝之官。这种作品的产生过程其实还不能称为创作,因为,第一,创作的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职责;第二,创作的时候指向神灵,不从现实感触出发。咒语和祷文可以说是诗歌的源头。《诗经》时期,“诗言志”理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诗经》颂的部分保留了感天地、动鬼神的咒语和祷文的部分特征,风、雅的部分则是新时代的产物。十五国风类似于民谣,由采诗之官加以采集整理,作这些民谣的人几乎不可考证,采诗之官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给在上位者作治国的参考,并不考虑做诗的人的本来目的。雅是正乐,似乎更倾向于是“在列者献的诗”,也就是士人献诗。这一部分的内容比国风更接近于统治者的意识,因此目标也更明确——讽谏颂美、正君主之得失。总之,《诗经》言志是指,诗歌表达讽谏颂美统治者的目的,讽颂更进一步的说,是为了辅佐君主治国,以君主为本位。采诗、献诗也是出于职责,是不自由的。“诗言志”的内涵,无论是咒语祷文言“神人以和”,还是《诗经》风雅表“讽颂治国”,都是指诗本身说的。后来出现的“诗以言志”则有些出格,它是赋诵朗读现成的《诗经》篇章,断章取义的表达自己在某个场合的意思。例如,在外交与朝堂宴会上,借现成的篇章作外交辞令或官方用语。这样的赋诗,赋诗的人是用已有的诗,表达自己的意思,看似有所选择,其实也是不自由的。孔子虽然未直接言及“诗言志”,但他的思想对“诗言志”的内涵却有所扩充,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仁”的角度出发,强调《诗经》表达的治国之志,应该以民为本,或是君、民并重。这是治国之志的一大进步。第二,为了更好的实现治国之志,先要有修身之志。这样,独善其身,自由的个人意愿有了出现的可能。诗人时期,“诗言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离骚》中个人感情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此后,诗的作者的问题日益清楚了,诗的形式、题材都大大扩展了,诗歌可以表达个人的志向情感了,不管这志向是讽谏治国,还是独善其身;是忘怀得失,还是忧国忧民;是赏花弄月,还是发愤抒情;总之是自由了,从个人出发了。这时期的“志”一方面不断吸收与其相关联的情感因素,打开了情志合一的大门;另一方面却严格的排拒了一些纯感情因素,通过志对情作出了规范。做诗的人在诗中自由的表达个人的心愿志向,这其实就是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总而言之,志的变化,由神人以和到讽颂治国,从神明到现实;又由为君为民的讽颂到出于个人目的的志向,从集体到个人。诗的本质,在“诗言志”的范围内,乃是一种工具,是志的载体,志变,诗亦变。诗的功用从悦神祭祖、治国修身这样重大的实际用途发展到了发牢骚、自娱乐、呈才气等等无功利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