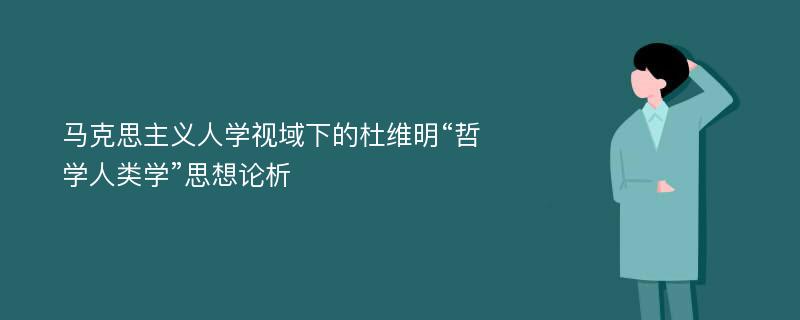
论文摘要
二十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面对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大环境呈现出的新特征: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民族文化的寻根意识渐趋加强;七十年代“亚洲儒家资本主义文化圈”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提出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界对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危机和人的异化问题的反省,人道观念、和平理想逐渐觉醒;以及在理论层面上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儒学以失去生命力”而“博物馆化”的断言。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先生,怀抱着创新儒学的历史使命感,在厘清“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将儒学诠释为一种站在人的立场进行哲学反思的“哲学人类学”,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他基于中国人特殊的自然宇宙观:“存有的连续性”这一本体论假设,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实现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转化的动态持续过程;并认为“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是一个宗教伦理问题”,儒家的人性自我的实现除了需要内在主体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外,还需要外在人际关系的层层拓展与交互作用中进行创造性转换。杜维明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儒家传统”才是儒学的本真,并具有历久恒新的恒常价值,可视为救治西方世界之人生意义没落的良方,以突显儒家人学思想固有价值的现代世界意义。应该承认,杜维明的“哲学人类学”对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趋势、现代性与传统认同的意义以及现代化与未来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反映了当代世界时代精神的需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儒学解释学并未脱离儒家人性本体论假设的先验主义色彩,也不能从根本改变内在与超越的断层问题及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契合问题。特别是其“创造性转化”方法仅仅是观念的诠释,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又缺乏历史条件的支撑,故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必须将文化的现代化放逐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改造中,以人观念的现代化为根本,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以政治现代化为保障。因为真正的“哲学人类学”承认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传统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处于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之中,人只有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才能使自身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