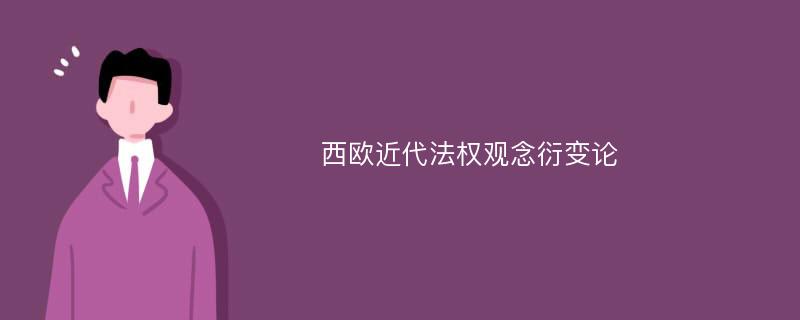
论文摘要
凡政治烙有文明的痕迹,无不是因为和法律联系在一起,但这二者的勾连却千变万化、形态万千。马克斯·韦伯作为西方文明之子,洞察到了西方法律理性主义的独特所在:唯有西方将“国家”与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规”作为本质性要素而结合在一个统一体内。因此,每一种政治变革必然都伴随着与之相连的法权的衍生和改变。16世纪上半期,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发生了永久性的分裂,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西方文明的内部爆发了分裂,基督教的统一世界彻底让位给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本文正是对这一阶段由近代西欧内部的政治变化所导致的法权观念之变革的探讨: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一直以基督教的术语被安置在一系列等级法权秩序中,西欧在走向近代之初还依然笼罩在基督教描绘的神圣景象中,但是,各君主国力量的增长加之宗教改革的震荡最终掀启了法权变革的大幕,理性崛起并逐步夺占话语权,借助对神权政治的彻底批判和步步围剿,力图构造并确立起合理性的政治、法律秩序,不过,古老的神圣合法性却是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全文分为五章并导论和结语共有七个部分。导论首先简要回顾西欧中世纪大一统的法权秩序: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各城市、庄园、教区、领地等被镶嵌在一个等级秩序中,各个等级之间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帝国代表最高等级,同时扮演仲裁人的角色,是臣属其下的各个政治单元之间的仲裁者,而帝国等级又被安置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中,因而,是基督教教义为大一统的法权秩序提供了最终的合法性;接着指出西欧政治演变与法权变革的共生性:西方法学在中世纪寄身于教会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则投靠了国家,“国家”代替“帝国”,成为近代法学构造的基本概念,新的法权秩序必然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最后说明本文的论述方式和基本思路:本文将在具体的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背景中,追踪和解析法权观念的内在演变,由此进一步透视不同民族国家内、异质的法权秩序如何从过去大一统的世界中分化剥离并获得独立,并试图检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道路的差异、优劣和得失。第一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概述宗教改革的背景,着重阐述基督教自然法观念和罗马天主教建立的等级制法律秩序。基督教(天主教会)因握有合法性的解释权而要求人们服从政治权威,同时也会随时以精神的名义反抗和瓦解世俗的政治权力;由于巧妙地保有教义的弹性和对权力的敏感,基督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团体演变为强大的权威机构并成功攫取世俗权力,最终,天主教会不仅成为封建法权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封建法权秩序合法性的来源。第二节阐释路德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等级秩序的冲击,这位德国的神学家通过倡导“因信称义”而彻底取消了教会在世俗中的法权角色,教会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法权单元,不能谋取世俗利益,因为灵魂的得救依赖的是内心的信仰,新的教会使无形的,不可能成为一个世俗机构;这种新教教义同时引发了对旧有的法权秩序合法性的质疑,这导致了旧秩序的重大转变。第三节探讨博丹的“主权”理论,博丹顺应君主国力量不断壮大这一形势,首倡“主权”概念,主权高于法律,并且创造和废止单纯的法律秩序;在博丹看来,惟有君主享有主权,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秩序;不过主权并非无所顾忌,主权背后隐含着某种制约因素,也即合法性的要求,而博丹认为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帝,因而主权也要服从上帝,服从政治体的根本目的,实质上是基督教伦理和古典善的某种糅合。第二章解析霍布斯“利维坦”的法权秩序。新教改革引发了宗教战争,博丹的合法性主张是混杂而无定论的,观念之争因而成为战争的一个根源,霍布斯对冲突和战争以及法权秩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思考,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关于法权秩序的主张:一方面他将一些引起争议的教义、善的观念贬斥为黑暗王国的东西,大力批判,而只留下争论各方都能够承认的“耶稣就是基督”这一共识性的教义,同时又吸收博丹的主权概念,构造出尘世的上帝——利维坦;另一方面,为了使这一人间上帝奠立于稳固的基础上,霍布斯用政治科学构造了自然权利理论。霍布斯依然把主权国家——利维坦视为法权秩序的单元体,不过其合法性基础已明显不同:基督教伦理以及古典德性被自然权利论替代,从批判黑暗王国到人间上帝、再到自然权利,霍布斯的思路清晰地凸显了法权秩序的理性化主张及过程。第三章分两节探究霍布斯之后的国家法权秩序的发展。第一节描述“绝对主义”的法权秩序: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反映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国家一旦从神圣训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快便淹没在追求物质利益、世俗幸福的欲望中,理性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相应地,君主的力量急剧膨胀,直至打破旧有的等级秩序,独享绝对权力,压制贵族等级,联手资产者巨大的商业力量;因此,理性绝对主义和君主专制相互呼应,一种由理性普遍法则构成的政治秩序被确立,这在法国君主路易十四建立的专制统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很快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不断响起,第二节讨论卢梭对这一秩序的批判和改变,这位现代社会的先知以德性的名义严厉指责因追求物质利益而导致的道德堕落,他接过了“社会契约论”学说,重新设置人的“自然状态”,以此为标准衡量和构造新的政治、法律秩序,通过将个体的意志普遍化,也即某种确立“公意”的机制,最终建立“人民主权”的国家。卢梭从观念上对近代国家的法权秩序做出了极为关键的变动,合法性从此不再诉诸于上帝,而是来自民众,由此决定性地使君主制不可避免地向民主制转变。第四、五章探讨康德构造的理性法权秩序。卢梭的批判依赖的是敏锐的感知力,康德则给出了真正的科学论证,将普遍的法权秩序明晰化并推进了对这一秩序的理解。在康德那里,法权秩序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之后而构造起来的法律王国,所以首先要探讨康德法权秩序的根基,这是第四章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各种观念岐见引发的冲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建立一个对一切事物做出评判的理性法庭,这是一部理性法规,确立了观念的法制秩序。而观念的法制秩序地建立依赖的乃是康德的“启蒙概念”,理性独享立法的权力,哲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期望能逐步引导大众走向普遍的理性状态。第五章具体展示康德构造的理性法权秩序。普遍的理性状态也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领域确立的“法则”状态,这既是他的道德律令的形式,也是法制状态的形式。“法则”和个体的行为规则总是表现得相悖,但恰恰是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制约保证了“法则”的实现,这是康德在个人主义和政治公共性之间达成的和解。正因为这种普遍的“法则”状态是超个人的,而康德又无法确信这种状态肯定会成为现实,所以康德不得不诉诸天意保证其实现。经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上帝”观念的彻底批判,在法律国度中又引入人类历史中的“天意”,至少在概念领域,康德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秩序模式,为各民族政治体在其历史中寻求“民族精神”的支撑开辟了空间。结语部分论述法权观念从世界主义向关注民族政治体的方向转变。康德的“永久和平”秩序还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启蒙理性的影响下而设想的,但埃德蒙·伯克已经开始激烈地反对这种政治、法律理性的普遍主义,他立足于英格兰的宪法制度和历史传统坚决拒斥以抽象规则为标准进行社会、政治的全面变革。时间老人才是智者,一切流传下来的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法权变革必须审慎,理论理性不能代替政治智慧。年轻的黑格尔也反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他试图吸收古典的伦理德性,并和现代理性主义融合在一起,将这种精神注入德意志的国家肌体。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撰写了“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德意志宪制”、“伦理生活体系”三篇重要文稿,期望构造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政治体,提出“绝对伦理”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实质性的伦理,并将这些伦理含义导入从私权体系到政体方式的各种法律制度中。在近三个世纪的衍变发展中,法权秩序从大一统转向分化割离,从等级制转向诸民族体,从帝国转向君主国——并伴生向民主政体的转变,从基督教的上帝转向历史中的天意,所有这些改变构成了一个祛神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