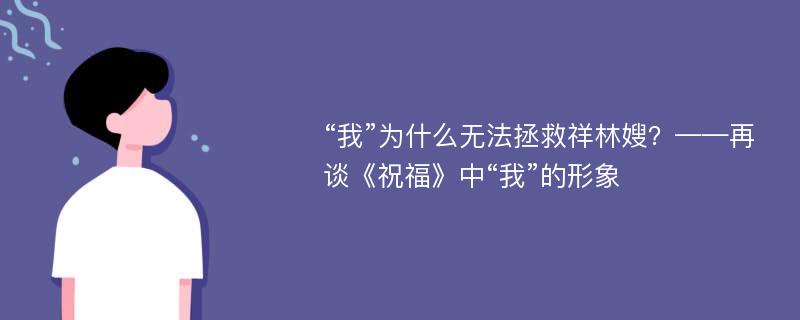
朱琳
摘要:本文主要谈论了《祝福》中“我”的形象,并分析了“我”和祥林嫂的死的关系。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关键词:《祝福》;“我”的形象;祥林嫂
鲁迅小说刻画了众多的“我”的形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绘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形象。《祝福》系《彷徨》第一篇。对于这篇小说主题的表述,一般界定为“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吃人本质”,文中“我”的形象,则界定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形象。但令人困惑的是,“我”既然是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封建文化道德对祥林嫂的层层催逼,为何听之任之、坐视不理呢?作为故事旁观者和叙述者的“我”和祥林嫂的死有没有关系呢?
一、漠然的旁观者
文中提到祥林嫂和“我”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是无过于她的人: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样子。”
由此不难看出,“我”和祥林嫂在五年前是见过面的。从后文“我”对祥林嫂遭遇的叙述之详细也可以看出,“我”对祥林嫂这一路的境遇非常了解。而“我”的身份的特殊性---祥林嫂的雇主鲁四老爷是“我”的四叔,“我”可以说是她的半个“主子”,也非常方便对她的了解。
祥林嫂的死,并非一人一事所致,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她是被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合为一股大绳,慢慢地拧紧窒息而亡,而“我”作为一个曾受过“科学”“民主”思想浸染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如鲁四老爷般残酷,也不可能如柳妈和众人般麻木,“我”应该能了解祥林嫂悲剧的关键所在,能够了解封建道德观念的荒谬与可笑。若在祥林嫂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我”能够稍加援手,对其进行必要的点悟,或许就会给祥林嫂的命运带来巨大的转机。这点小小的举动也许无法撼动封建道德观念在鲁镇的深深根基,至少可以给眼前的祥林嫂带来最起码的一丝光亮。
我们甚至可以乐观地想象,祥林嫂命运的转机,也许能给冷漠如荒原般的鲁镇带来一丝如春风般的希望,如蝴蝶效应般对这里的人们产生无法预知的影响。但“我”却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形象游离于这个故事之外。可能“我”并不缺乏同情心,但这种以双双泪眼、声声唏嘘观看“落水者”的心态和鲁镇中以咀嚼祥林嫂悲剧故事为乐趣的老女人们又有何异?不过是另外一种漠然的看客罢了。具备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许仅仅把所谓的新思想作为在城里呐喊的资本,无法运用到实践的层面。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在幽深而古老的中国乡村,甚至激不起半点涟漪。
二、徒然的参与者
旁观者一方面以眼泪为载体,播洒着自己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以双手塞耳,拒绝着“落水人”的呼救声。纵然自己做了“落水人”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徒然无功,白白增加了对人亡水静的哀叹。
一个不仅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和祥林嫂有了最后一次会面的机会。面对着眼前曾经相识的祥林嫂,我的表现是耐人寻味的。“我万料不到”,只能“诧异的站着”,这里充分说明“我”对祥林嫂的轻视,“我”原预备她来讨钱,“我”也准备用钱来轻易打发祥林嫂,但祥林嫂的问题是几个铜板能解决掉的吗?我的高高在上的优越者心态展露的一览无遗。
祥林嫂冷不防给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
当“我”发现祥林嫂竟然怀疑起人死后灵魂的有无来时,对于这个问题,“我”“紧张得就像遭了芒刺一般,甚至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偏是站在自己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这可真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文盲而且是一个将死之人给一个自以为见多识广且进步新潮的知识分子的考试,“我”该怎么来回答呢?当祥林嫂提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吧,—我想”。当祥林嫂顺着他的回答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时,“我”只得吃惊地支吾着:“地狱?—论理,也该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当祥林嫂接着又提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只得“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楚……,其实,究竟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一个长期在外,接受着新思想熏陶,有着比故乡人更多见识的“我”,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就这样支支吾吾敷衍了事地回答了,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还挺为自己能用“说不清”三个字敷衍祥林嫂深感自己的巧妙圆滑。因为用了“说不清”三个字作回答,自以为就没有了什么责任并可以事事逍遥了。“我甚至还认为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说不清”这三个字也是万不可省的”。“我”和“讨饭女人”成了两个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的对立体。这里实际上又真实而深刻地讽刺了“我”的对劳动群众的无知与冷漠,“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也还是”三个字显然是对“我”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决然否定。
如果说以前的祥林嫂落入水中之时,“我”还只是旁观者之一,无动于衷,也比较符合中国看客们的天性。但此时的“我”却是和祥林嫂唯一面对面的人,甚至可以说“我”是祥林嫂此刻唯一的救命稻草。“我”的行为直接关系着祥林嫂的生死,但“我”却吞吞吐吐着,就如同面对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如果有一句善意的谎言,或许可以延续她本不健康的生命。但“我”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却似乎给了她一个更为可怕的答案。“我”或许参加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和“运动”,但这些东西都高高漂浮在劳动群众之上,知识分子将自己自然的摆放在了神坛上,他们一方面在指责着封建的牛鬼蛇神的不对,另一方面也在堕落为新的神主。这一次的会面,是“我”唯一一次“被迫”参与营救祥林嫂的机会,也是祥林嫂的眼睛最后一次看到希望的亮光,但“我”的这种徒然的“说不清”,却直接将其推向深渊。“我”成了祥林嫂之死的直接推手。
三、醺醺的逃避者
“我”于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面对着有“乡”无“家”的现实,面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祝福”习俗,面对着空中弥散着的幽幽的火药味,鲁四老爷的保守与顽固,众人的愚昧可笑,有极度的不适应。“我”也仿佛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新客,和此地格格不入了。比起外面的世界,“我”已然明白了故乡的保守与落后。
当“我”以一句“说不清”搪塞了祥林嫂最后一次疑问,也曾经有略微的不安,但这带着略微不安的大脑在不久以后便就被福兴楼清炖鱼翅的香味所替代,随后就只余下“舒畅”的感觉了。在“祝福”的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惰而且舒适”,此时的“我”,真的化身为“醉醺醺”的天地圣众了。祥林嫂的死,非但没有促“我”立即离开鲁镇,却让“我”能够更加畅然的享用这祝福的盛宴,享受祥林嫂们准备好了的祝福的“牲醴和香烟”。
“我”由格格不入者变为了逃避者,由逃避者变为了接受者,由接受者变为享用者了。这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人们的无限的幸福,也只有播洒与那些供奉着“牲醴和香烟”的鲁四老爷们的身上了。广大的麻木的人们在鲁镇密封的大环境中照例过着自己“应得”的日子,那牢不可破的天罗地网还依旧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默默密织着。而此时的“我”,和鲁四老爷又有何异呢?可能只是鲁四老爷和阿牛之间的承接者罢了。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我”继续留在所谓的故乡,将来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如果说封建的文化与道德是一个强大的磁场,“我”确乎曾经做了短暂的游离,但一旦再次回到这个大酱缸里,便又逃脱不了被染回原色的命运。
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曾为思想先驱者们在中华大地上高高擎起,但处在城乡高度分离与对立的旧中国,所谓的新思想也只能如水莲花般浮于水面了。“我”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受了新思想的浸染,但一旦再次进入如酱缸般的“故乡”,又必然会有了旧时的颜色。“我”或许曾经为新思想摇旗呐喊,但这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了,没能有具体的行动。沉睡于铁屋中的人们,曾经庆幸于几个人的呐喊,但呐喊之后会怎样呢?腐旧的社会,害人的思想,锈蚀的灵魂,人肉的宴席依然在眼前不断上演。
“五四”高潮退后,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闷,鲁迅先生也感觉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自选集•自序》)他也曾“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呐喊•自序》)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深刻反省和对未来的思索。《祝福》除了沿袭了鲁迅先生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主题,更多的是对当时的“启蒙者”本身的深深质疑。封建主义是僵死的活动,革命战线又分化而“布不成阵”,他就成了二者之间最大的孤独者,所以只能是“荷戟独彷徨”的结果了。《祝福》中的“我”身上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软弱、妥协与退缩,也表现出了他们和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甚至对立,更可怕的是他们的不自觉的退化与堕落,又变为了封建文化与道德的帮凶与代理者。“我”遥望着祥林嫂们的悲哀,但无法伸出拯救的援手。时代似乎走入了困顿的泥淖之中,呼唤着更加强烈而彻底的革命。
作者单位:陕西省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邮政编码:71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