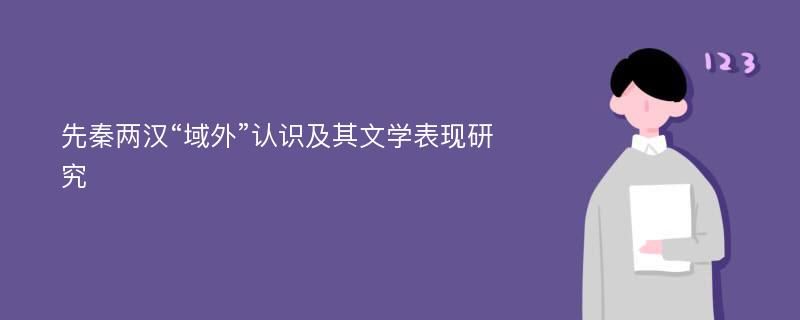
论文摘要
先秦两汉时期中原与域外交流不断扩大,经历了由萌芽到逐渐深入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原人民对于域外的认识随之不断变化,其自我中心意识也渐趋鲜明。本文即从先秦时期人们的“域外”认识入手,述及汉人在国家意识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明确,并着重分析先秦两汉文学对“域外”认识的表现。通过考察先秦时期人们的“华夏”观念,我们发现,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先秦时期,人们主要从生产生活方式与是否具有“礼”两个方面对中原与域外加以区分和认识。先秦人们认为,农业和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原周人所独有的特征,而其他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的民族则被中原人们主观地视为“异族”。礼文化可以视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代名词,不具有礼的异族被排除在中原正统之外,甚至被视为禽兽。在这种对域外认定的基础上,先秦文学中也不乏对“域外”认识的表现。首先,在先秦文献中十分强调“华夷之辨”。如《左传》以“礼文化”为标准,将中原与异族两大形象群截然分开,与正统的中原文化相比,异族始终处于落后野蛮的状态中,并被中原文化所鄙视。这种观念在《诗经》的有关篇章中也有体现,《诗经》作品在描写与异族的战争时,侧重描写中原军队的声威,对异族敌军的情况只是“轻描谈写”,以期突出中原民族的正统崇高地位。其次,异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是先秦文献表现中原文化崇高地位的又一途径。吴、楚等异族均以各种方式学习中原文化,接近中原文化也是其在争霸中取胜的途径之一。《山海经》也其独特的方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夷夏观念。书中所载异国数量伴随其地区距“山经”(中原)距离越来越远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正是先秦人们部落中心主义的体现。《山海经》的作者又以“山经”部分(与中原对应)对物占与祭祀权的把握表示着中原文化在各个地区中所占的崇高地位。这直接造成了在《山海经》的记述具有夷夏分明的特点。和先秦时期人们的“华夏”观念相应,伴随着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展,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逐渐明确。在汉代文献记载上呈现出“实录”与“想像”两个系统。“实录”者以史传文学为主,《史记》以对异族族源的重构展示了汉人心目中的大一统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中,汉代史家将各地的风俗收入其所制定的史书及文献中,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试图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也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一改先秦排斥异族习俗的态度,而代之以兼容并包的策略。在具体统治中,汉朝还派驻循吏以儒家之道教化边鄙之民,这使汉民族的文化基础进一步牢固,中原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汉族对异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与正史记载相应,汉代纬书当中还存在一个域外想像的世界,其来源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继承《山海经》等上古神话的异方描述,呈现出较多的神异想象色彩;第二类,来自汉代与域外的交流,描述上较为接近现实,但这零星的真实与纬书的奇幻氛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经过分析我们可知,汉代域外记载的两个系统并非截然相异,二者都有对现实描写和想象虚构的成分。汉代域外文化对于中原的影响还体现在诗、赋等文学样式上。乐府诗中的横吹和鼓吹曲皆引进自域外。鼓吹乐在汉代颇为流行,其原因与异族影响密切相关:其一,与鼓吹乐所使用的演奏乐器有关。西域民族有迁徙游牧的特征,故其乐器适应这种习俗而呈现出简便易携并适于个人演奏的特点,在音乐演奏中呈现出较强的节奏感和灵活性。其二,鼓吹乐更符合汉代人新的审美需求。异族音乐的传入是杂言出现的催化剂,它赋予诗歌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它的出现更符合汉人新的心理欣赏需求,为汉人广泛接受。伴随对西域用兵的需要,西域天马成为汉代诗歌中具有独特意义的意象,天马既是张扬大汉国威的象征物又承载着汉人求仙长生的愿望。此外,由于与西域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在诗歌当中也出现了以《羽林郎》为代表的以西域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也受到来自西域的影响。汉赋中异域地理名称大量出现,使赋作体现出宏阔的空间感;来自异域的事物极大丰富了汉赋的内容,更有利于表现皇家的奢华,满足了汉赋作家以铺排方式赞颂大汉王朝的需要;异族技艺也是汉赋作家们关注的对象。此外,由于武帝时期对外族用兵的需要,校猎军训的意图更加明显,校猎赋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异域之风对汉赋总体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更有利于体现汉代文化宏大恢廓的气势和汉人的浪漫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