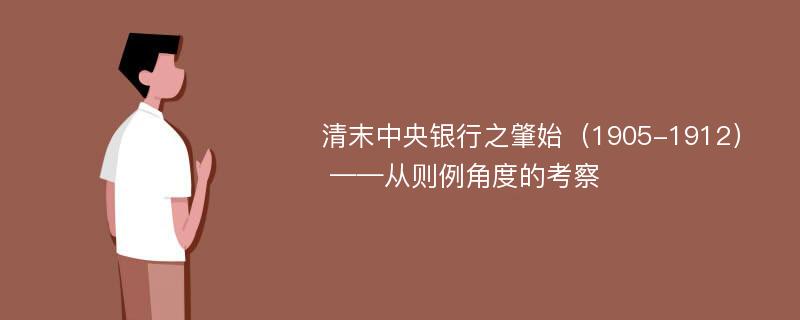
论文摘要
由于辛丑条约以及推行新政对国家财政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同时政府也希望通过建立现代化的银行机构以实现整齐币制、规范金融市场的目的,加之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提供的实践经验,清政府最终于1905年正式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为保障其实现开源的目的,《试办银行章程》从业务的规定与治理模式的选择入手,并在符合《公司律》的规范要求下,采择日本模式进行中国式的调整,尝试西方银行制度的移植。比如采用“双层董事会”模式,但监事会成员由股东选举通过,取代政府任命;与本国已有金融机构合作设立分号,以降低设置成本等。不过,由于经验不足,户部银行制度也存在着“专注获利”、缺乏专职管理人员与股本筹措波折的问题。试办三年多后,因从属上级——户部与财政处合并为度支部,以及自身中央银行地位明确的必要,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而其法律依据——《大清银行则例》也在名称、条例数目以及内容方面与《试办银行章程》多有不同,制度架构与人员委任方面规范性大增,且政府角色更趋明显,银行对市场规范的职能承担度加强。但放款类型、股东与会资格认定等的模糊规定仍使大清银行制度存在部分缺漏,特别是厚德银行案所体现出的大清银行则例内容与执行的脱节,更是大清银行经营失败的根源。尽管因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属性,银行制度与我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体现出的完全不同的管理机制,前者建立在“法”的内涵上的“正规制约”,而后者更多的受到我国传统宗法文化下的家长制影响,由此引起两者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与制度建设方面的巨大差异。然而,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建立时面临着专业人才缺乏这一关键难题,大清银行在人事制度、会计制度方面,仍然受到了传统文化极为强烈的影响。如以人员的阅历与地域联系取代对知识、能力考察的注重;以内部举荐方式取代规避制度,同时在管理者职业背景、权限等方面与钱庄、票号也存在着相似性。正是由于清末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由政府主推,以缓解日益困难的财政危机的前提,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选择了具有相似背景与建立目标的日本银行作为参照对象,并且极为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因银行制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先天差异,在银行规范性不断提升而传统文化并未相应变革的情况下,引发的是文本与实践的偏离。由此,对制度移植而言,其必然经历外来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博弈历程,而“本土化”的成功在于以正规约束为代表的外来制度与非约束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达到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