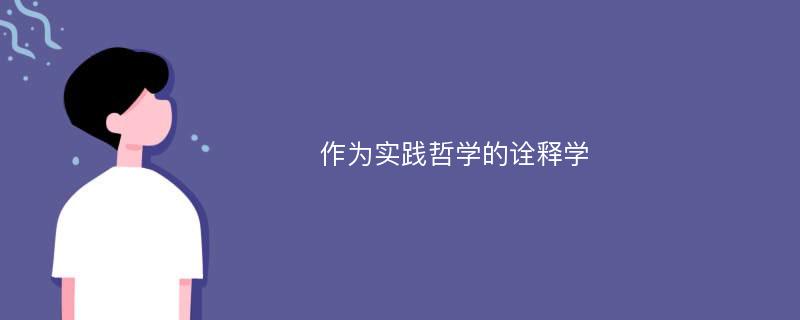
论文摘要
西方诠释学传统自发端以来,就暗含着实践的因素,对于法律规则与神学戒律的诠释始终离不开现实的应用,只是由于浪漫主义诠释学的遮蔽,人们才对这科,因素视而不见。伽达默尔对“诠释学基本问题的重新发现”就是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显现出来。伽达默尔的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实践哲学的传统,将其与本体论诠释学结合起来,提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之后,伽达默尔连续发表了《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等文章,对其诠释学理论从实践哲学角度作了详尽的评述和总结,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也就成为伽氏思想的合理创见。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直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概念,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纯粹科学、应用科学或技艺的概念,最终使科学的自然知识和实践的人文知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实践智慧的应用之间的区别明晰地显现出来,借助这一区分,伽氏认为实践智慧本身即是一种道德行为,对实践智慧的强调就使伽达默尔重新发现了诠释学的应用问题,促使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与诠释学中理解的应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亚里士多德有关实践哲学的分析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属于诠释学任务的问题模式。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思想在《真理与方法》中的表现就是伽达默尔对理解的应用性问题的重视。理解的应用性问题首先表现在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应用,伽达默尔通过法学诠释学与神学诠释学的典范意义阐明了这一点,同样,古老的语文学诠释学中也始终包含着应用的成分。理解的应用性还表现在理解本身即是一个语言应用的过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就如摹本和原型的关系,正如摹本具有使原型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功能一样,语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作用。所以,伽达默尔不仅把语言性作为诠释学对象之规定,作为诠释学过程之规定,而且将语言性作为诠释学理解模式之规定。《真理与方法》发表后,伽达默尔走向了更广阔的实践哲学领域,其深层的原因是一方面在于为人文科学寻找独立性与合法性的努力,另一方面在于尝试摆脱其理解理论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倾向。后期伽达默尔将其诠释学用于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在诠释学的实践维度与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维度上重新厘定实践与理论的概念关系,认为实践并不只是理论的实际应用,理论也非脱离实践的理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追求一种理论与实践任务的统一。同样,随着近代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胀,实践理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被它们所取代,人类失去了自由的生活状态,整个社会陷入技术统治之下,此时就迫切需要恢复实践理性的本来面目,强调实践理性的实践哲学思想才是人类社会正确生活的指导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最终理想是发展出一个以友谊、善为目标的对话共同体,对话精神不仅是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紧张关系,缓解科学与社会冲突的有力武器,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未来发展的合理理想。伽氏试图通过理论的建构来为人类未来发展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处于同一时代并与伽达默尔产生激烈论战的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出路就在于一种“交往共同体”,这似乎就与伽达默尔的努力处于同一道路之上,事实上,通过对他们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知,双方强调对话与交往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且双方理论可以达到彼此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