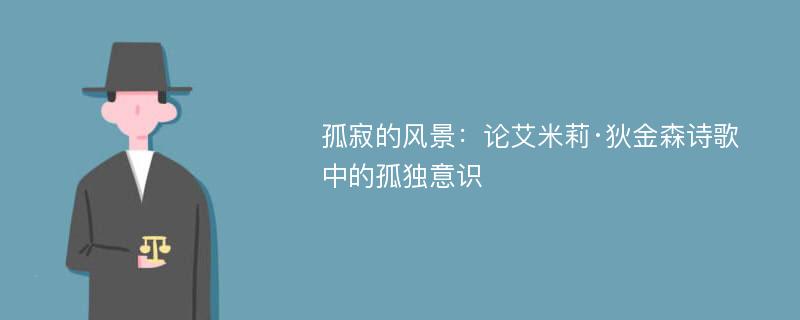
论文摘要
作为当今世界文坛所热衷的神秘人物,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以其传奇人生及独特创作在文学评论界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沉浮:生前默默无闻,而今则广受欢迎,且其盛名与日俱增。早在1924年,康拉德·艾肯便将狄金森的诗歌誉为“英语创作中最出色的女性诗歌”,此可谓一语中的。狄金森的一生扑朔迷离,而诗歌则大多晦涩难懂,这与她生前的隐逸生活不无关系,也是国内外狄金森研究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狄金森偏向内省、离群索居,然而,其诗歌想象中构建的世界却丰富多彩,并具有恢弘的感知空间。狄金森在家宅中孤独终老,虽困于二楼卧室的逼仄空间,但其诗歌却以全景式视角阐释宏大的主题,譬如,宗教、自然、爱情、生死、永恒等。无论表达方式还是内在涵义,狄金森的诗歌都不会给人以狭隘及单调之感。然而,在其诗歌世界中,狄金森也展示出内心强烈的孤独感及痛苦。诚然,诗人弃绝正常的人际交往及社会活动、凌驾于尘世之上的孤寂生活似乎是其孤独感的根源,但在细致审视之下,狄金森的孤独感超越了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孤寂,进而被放大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心体验,而这归根结底源自诗人在19世纪新英格兰浓重的宗教社会背景及其在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文化中的离经叛道。狄金森坚持认为,孤独是人之为人的固有特性,而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行旅。此外,狄金森在人与自然的思考中获得了某种清醒的超然,认为天人合一无望实现,而人类在面对自然及宇宙时存在一种集体孤独感,这进一步增强了诗人的孤独意识。狄金森在诗歌中阐释自己对宗教、自然、生死及永恒的观点,但其矛盾及多变性给读者的解读带来重重障碍,而诗人对传统诗歌格律、语法规则及措辞的背弃及其诗歌中诡异独特的意象、简洁多元的内涵加剧了其诗歌批评的复杂性及困难性。狄金森宣称,其诗歌中的言说者并非自己而是“假想者”,尽管这预示了现代诗歌的创作观点——虚构叙述者,然而,狄金森的诗歌、书信及传记资料无一不在印证着同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狄金森诗歌中的“我”为诗人自身说话。在狄金森研究中,经常出现鲁莽判断、简单化甚至是歪曲的解读,鉴于此,本论文力求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并将狄金森置于相关历史与文化语境中,以期获取更为可靠的文本解读及观点论证。论文中采用存在主义视角阐述狄金森的黯淡生死观及其对宗教、自然的哲学思考,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被用来诠释诗人在19世纪父权制社会及父权诗学下的生存状态及作者身份焦虑。此外,本文采用精神分析法对狄金森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和解析。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首先对孤独进行定义,并确定孤独在文中的内涵及措辞。在陈述本研究的意义目的及分析方法之后,文献综述部分对中外狄金森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进行梳理,为后文的论述奠定基础。第一章阐述狄金森因对19世纪新英格兰制度宗教的反叛而遭受孤独之苦。狄金森对宗教的态度犹疑不定、矛盾重重,使人很难轻易界定其宗教观。在19世纪新英格兰浓重的清教氛围中,狄金森渴望得到上帝的认同及庇护从而获得信仰上的归属感,但在关乎上帝拯救能力及灵魂归宿的关键问题中,狄金森认清了上帝的冷漠、无能、虚伪以及残忍,从最初的信仰及渴望转而成为一名怀疑论者。在科学及地质学发展带来的世俗知识的普及及启蒙下,狄金森在膜拜上帝及来世救赎等问题中获得了一份清醒。美国内战进而粉碎了诗人渴望上帝赐福的梦想,使狄金森在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转而投向自然寻求精神的慰藉和依托。狄金森远离教堂,将自己置于反叛之地。在弃绝制度宗教的过程中,狄金森脱离了信仰的群体,而家人及友人的相继皈依更使其倍感孤立,随之带来社会维度上的孤独感。尽管家人及友人一再劝说而诗人自身也不断努力,但狄金森最终无法逃避自己的质疑与清醒,未能成功皈依。然而,狄金森终其一生奋力挣扎在热望与拒斥之间,而其中的犹疑和摇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疏离感和孤独感。在对制度宗教失望之余,狄金森致力于其个人信仰的发展。她在追求真理与美的过程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冥想实践着爱默生的理念:转向自然,以人的直觉感知力去发现真理与美。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狄金森都怀有一种童真情结,为其对世界的观察及对顿悟的直率表达提供了一种纯净的童真视角。狄金森的童真信仰为其创造了新奇的诗行,而作为一个身心远未成熟的成年人来说,该视角则将其置于真实世界的孤立之地。第二章论述狄金森在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中所产生的孤独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中的孤独、生命中的孤独、死亡面前的孤独。在该过程中,诗人体验到强烈的生存孤独感或宇宙孤独感。狄金森认同浪漫主义者尤其是爱默生的信条:自然是美的体现,而人可以从对自然景物的直接观察或深入冥想中获得美的享受。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自然是高度人化、内化的自然,投射着诗人的内心世界。然而,狄金森通过敏锐的观察及直觉的感知却洞察到自然的另一面:冷酷、淡漠,甚至具有摧毁性。狄金森更多地继承了爱默生的怀疑论,并展现出一种清醒的自然观,强调自然的无常及神秘莫测。对狄金森而言,自然存在固有的运行规律,无论人类的努力或愿望如何,自然之谜终究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人与自然无望达成最终的统一,而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则成为狄金森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尽管狄金森在诗歌中赞颂生命的的狂喜,但综观其创作,狄金森对人的存在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她认为人是孤独的朝圣者,并将人的存在定义为孤独的行旅,自始至终都要面对生离之苦、死别之痛。生命稍纵即逝,狄金森在隐遁生活中仰仗与朋友的交流获得必要的情感满足,而朋友出于各种原因的别离则加重了诗人的孤立境地。同时,诗人在与父母的疏远关系中遭受严重的情感饥渴。狄金森的父亲严肃而孤高,而母亲则柔顺孱弱,无力在狄金森性格形成期及成长过程中为其树立健康的女性榜样及精神支柱,这也成为诗人内省性格及压抑个性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狄金森在爱情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加重了其情感缺失所带来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尽管有评论家认为,狄金森选择独身生活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决意摒弃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设定的标准并以此表达对父权文化的抗议,但无论如何,狄金森在父亲的大房子孤独终老是不争的事实。她在形单影只的生活中饱尝孤独之苦。狄金森在诗歌中展现了一个为死亡所困扰的人格。她将死亡视为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而灵魂的永生则是个不确定的命题。死亡的迫近与威胁造成人类生命中本质的孤独,体现在狄金森有关分离、丧失及痛苦等主题的诗歌中。在死亡阴影的威胁之下,人在此世的生存令人沮丧,而对于有可能再续团聚与幸福的来世,狄金森则表露出莫大的怀疑和不确定。狄金森怀疑来世的真实性,但对于灵魂的不朽又持热望,其间界限难以确定。在对来世的构想中,狄金森在笃信与怀疑中摇摆犹疑,无力作出最后抉择。第三章将狄金森置于19世纪新英格兰的历史语境中,解析诗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文化中所遭受的性别孤独。狄金森的孤独源于其作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及其作为女性作家在父权诗学中遭受的作者身份焦虑。作为19世纪新英格兰父权语境中的异类,狄金森经受着文化维度上的孤独感。由于家境殷实,加之父亲声称支持女性教育,狄金森得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初级教育,但诗人却无缘更为深入的教育及社会参与机会。究其原因,其父亲代表的社会女性教育理念是主要因素:女性教育应该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准备。在承担家庭琐事之外,狄金森开始诗歌创作,然而,其创作欲望及天赋却无人关注。无论在社会背景还是家庭背景中,狄金森都是被忽视的,生存在沉默之中。在19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然而,整体说来,女性写作遭遇父权诗学的压抑和阻碍。在性别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狄金森的随性写作方式备受维多利亚审美标准的诟病。狄金森表现出对公众认可的热望,却拒绝对男性建立并守护的传统标准刻意逢迎。她无视传统诗歌的格律要求,甚至摒弃语法规则,将诗歌作为其心理困扰的自然宣泄。狄金森深知,这些有悖常规的做法会使其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举步维艰,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拒绝作出实质性的修改。狄金森虽时刻准备放弃社会认可,却无时不在寻求以隐藏的方式并借助另一种文本策略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采用“虚构”的叙述者及阳性人格,狄金森几近女性主义者们所谓的“双性同体”,然而,她也因此遭受自我的分裂,并陷入心理维度上的孤独感。狄金森曾在宗教信仰中茕茕孑立,而今又在父权社会的压制下坚守反叛的阵地,深切感受到世界的孤立和遗弃。第四章深入探讨狄金森孤独意识的性质,并指出其双重性:孤独中的痛苦焦虑以及独处中的浪漫体验。在对制度宗教及父权社会的反叛中,狄金森与世隔绝,丧失归属感,而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超然思考中,其体验进而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孤独意识。此外,从存在主义视角看,狄金森对生命及死亡的审视也使其产生强烈的疏离感,而天堂或来世的虚幻性则使此生更为黯淡压抑。无论何种维度,狄金森的孤独感都无一例外带来焦虑、痛苦、恐惧等负面情绪,并在其诗歌中反复出现。狄金森在孤独中遭受的痛苦经历了渐近的过程:从最初的感伤、忧郁到后来摧毁性的压抑,后者甚至使作者一度生出自杀的念头。在其死亡诗歌中,狄金森的叙述者站在死亡的彼岸诉说着似乎无以言传的体验,狄金森更在诗歌中展现具体的自杀过程,将自主结束生命看作对人生苦难的必要解脱。在狄金森的诗歌中,除弥漫着压抑的孤独之痛外,还有一种旋律不容漠视:对独处的称颂。狄金森从独处的寂静时光中获得审美的满足感及冥想的空间,她实践着梭罗的理念——孤独是最好的伴侣,并以此保护自己的本真,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空间。诗人遁出喧嚣的尘世,从而进入到一片更为广阔的诗歌想象世界,在此,她追寻着自己质朴的信仰,弃绝了父权诗学的束缚,成功地保存了自我及个性,而当今世界才得以获得她近2,000首清新质朴、别致独特而又思想厚重的诗歌。孤独成为狄金森诗歌灵感的源泉,并激发了其创作潜质。狄金森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沉潜地思考,并以不同的文本策略及迂回的方式实现着自己与社会的交集,将自己的沉默变成一种“对话式”的言说方式。孤独成就了诗人的自我审视及自我完善,为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作了新的诠释。狄金森深居斗室,却因此而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广阔视角和胸怀,而拜这种视角所赐,狄金森的诗歌虽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却从来不曾让人觉得狭隘或无趣。论文的结尾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并得出结论。狄金森在默默无闻中度过寂寥的一生,而孤独在其生命中挥之不去。狄金森坚持听从心智的呼唤,信守质朴的真理,从而拒绝了制度宗教。在看清上帝及天堂的虚伪面目之后,狄金森转而内省,坚持童真信仰,并在真理与美的不懈追寻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个人信仰。由于宗教观截然不同,狄金森与家人和朋友渐行渐远,在反叛中踽踽独行。从存在主义视角看,狄金森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获得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清醒认识,而人与自然的疏离成为诗人孤独意识的重要源泉。在其存在孤独感中,狄金森将人生看做一场孤独的行旅,充斥着死亡带来的分离与失去,而来世不过是虚妄。在19世纪的新英格兰,狄金森作为女性及女性作家在父权语境中备受偏见,遭受着性别带来的孤独感。她在追求文学创作的社会认可过程中备受创伤,其诗歌光芒被父权诗学的权威所遮蔽。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意在为狄金森的孤独正名:其孤独感无论在含义还是后果方面都具有双重性。除带给诗人痛苦、焦虑甚至恐惧之外,孤独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被部分转化为一种平和的慰藉力量,并成为其生存及诗歌创作的沃土。孤独带给狄金森必要的宁静生活及冥想空间,进而保存了其作品中的个性及独创性。狄金森在孤独中对生死及自然的审视获得了更为恢弘的视角,从而生出敏锐的洞察力及智慧的顿悟。狄金森在孤独中与自然和世界直接相遇,沉潜地观察并思考,而对繁杂的人间事物则保持了某种清醒的超然,颇有几分道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概。狄金森遁出尘世,却并未与世隔绝,而通过将其沉默变为另一种言说及抗议,诗人以迂回的方式实现了隐藏话语的表达。狄金森的诗歌是其自我的直接投射。在仔细审视其诗歌世界的基础上,本论文旨在洞悉狄金森的孤独意识,并希望以此阐明狄金森对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及世界文学的贡献。同时,本文力求展现一个可信的狄金森形象:弥漫在她生命及作品中的孤独,除却其腐蚀性外,已然上升到一种生存哲学的高度。对狄金森而言,孤独是一种彰显人的意志品质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她的诗歌也因此成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方独特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