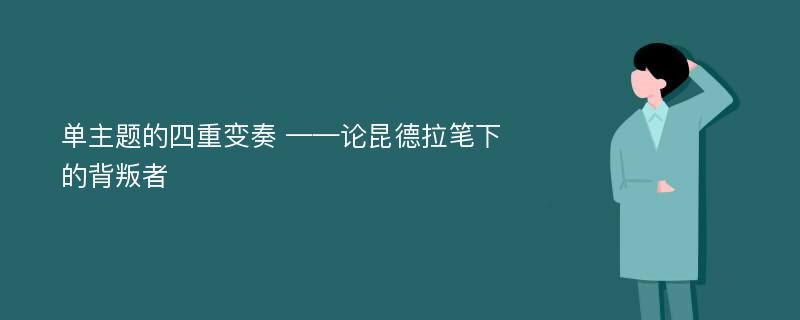
论文摘要
纵观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从《玩笑》开始,到创作的顶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再到近年来的法语三部曲《慢》、《身份》、《无知》,可以看出作家的自我个人色彩是非常浓烈的。首先就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昆德拉从来不按照正常的时序来叙事,他笔下的情节,大多都是模模糊糊、时空错乱的,而且在叙述过程中经常加入自己的哲理思考散文,甚至把自己当做小说中的人物,参与到故事的情节中来。比如《不朽》、《慢》等。据他自己在《小说的艺术》中表态的,这是对十八世纪的拉伯雷、塞万提斯等文学巨匠的小说的一种继承和致敬;第二,就是他小说中那些奇特的人物形象。昆德拉所做的就是粉碎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以来那股高度仿真的潮流,他的小说人物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他们有情感,有过去现在未来,不过小说人物并非他小说的结构中心,他们只是昆德拉用来思索和拷问存在而创作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些角色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实验性的“自我”,“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这些人物比起我们现实中的人物可能有些夸张的距离,但却能深刻地打动到我们,因为他们仿佛就是是我们梦境的延续。昆德拉在他的“存在研究室”里探索了轻、重、媚俗等深刻的命题,而背叛,是他笔下的一部分人物采取的直面现实、感受存在、寻找自我的救赎方式。本文从昆德拉所创作的《玩笑》、《告别圆舞曲》、《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身份》、《无知》等八本长篇小说入手,从中抽取出某些共性,把这些背叛者用作者自己的术语“变奏”逐一归类:放荡者、神性女子、媚俗者以及流亡者。本文结合各种作品和理论,阐释了这群背叛者的形象意义和文化含义,否定了昆德拉头上那顶学界许多学者前辈戴上去的“诗意沉思者”的帽子,认为他实际上是极为冷静的旁观者,正是他那睿智而虚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使自己笔下的背叛者再怎么挣扎也无法摆脱世界的各种陷阱。
